《我们的孩子》是美国当代政治学家罗伯特·帕特南的最新作品,用“以点带面”的叙述方式,展示了美国社会在过去半世纪以来日渐扩大的“阶级鸿沟”,讨论了穷孩子和富家子在成长过程中所经历的全方位差距。
全书反复出现的一个意象——贫富阶级之间的“剪刀差”——在家庭结构、父母教育方式、学校教育、邻里社区内都有鲜明的反映。在这个生而不平等的时代,仅仅谈机会均等是不公正的。

美国梦:幻象与现实
我回到了俄亥俄州,但记忆中的故土已然消逝。
如果我能真正理解都柏林,那我也能
理解这世界上的所有城市。
在一粒沙中,我们看到整个世界。
我的故乡,回到20世纪的50年代,正是美国梦的一处梦乡,在那个名为俄亥俄州克林顿港的市镇上,所有的孩子无论出身,都能获得体面的人生机遇。
但半个世纪过去后,克林顿港的生活却已成为一场美国噩梦,整个社区被划分成泾渭分明的两部分,两边的孩子各自驶向彼此不可想象的人生。早在出生的那一刻,孩子们的命运就已经被决定。
不幸的是,克林顿港上演的悲剧只是美国社会现状的一个缩影。这种转变是如何发生的,它为何与我们息息相关,我们又应如何行动起来,改变我们社会被诅咒的命运——这就是这本书将要讨论的问题。
从现有最严谨的经济和社会史研究中,我们可以看到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景况,当时,小到克林顿港,大到整个美国,社会经济壁垒处在一个多世纪以来的历史最低点,具体表现为:经济和教育高速发展;收入平等程度较高;邻里和学校内的阶级隔离维持在低水平上;种族间通婚和社会交往的阶级壁垒也可以轻易打破;公民参与度高,社会凝聚力强;出身社会下层的孩子们有着充足的机会去攀登社会经济的上行阶梯。
克林顿港是个小地方,种族构成也谈不上多元,但从其他各个方面来看,克林顿港确是一个可以代表20世纪50年代美国的微观缩影,从人口、经济到教育、社会,乃至于政治,都是如此。(克林顿港是渥太华县的县府所在地,而渥太华县则是美国风向州中的风向县——也就是说,渥太华县的选举结果在历史上总是最接近全国范围内的结果。)
我高中同学的人生故事向我们展示出,无论贫穷富有,甚至无论肤色黑白,所有的孩子都有机会走向成功。在我的班级上,贫穷的白人小孩唐和莉比,贫苦的黑人小孩杰西和谢丽尔,还有弗兰克这位我们班级内唯一真正的富家子弟,他们的人生能走多远,首先取决于他们自己的才华和进取心。
美国之大,没有哪一个市镇或城市可能完美展现国家的全貌,况且50年代的克林顿港也并非人间天堂。这里的少数群体遭受着严重的歧视,女性甚至经常为社会所边缘化。正如我们在本章接下来会进一步讨论的,当时美国的社会问题在克林顿港亦无从回避。如果不经大规模的社会变革,现如今恐怕没什么人愿意重回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我也是如此。但社会阶级在当时并不是决定人生机会的主要因素。
但是,当我们的目光投向21世纪的克林顿港时,现如今富家子弟和穷苦孩子所面临的人生机会已经有了天差地别,从我们接下来将会读到的切尔西和大卫的人生故事中,即可见一斑。今天的克林顿港,随处可见壁垒森严的阶级隔离,按照学校官员的说法,校园内停泊着阔绰富家子弟的敞篷宝马车,与之一步之遥的是他们贫穷同学的破烂老爷车,有些人无家可归,每晚把车开走后就睡在车里。
发生在克林顿港的种种变化,涉及经济环境、家庭结构和父母管教、学校和邻里社区,而克林顿港的新故事又是整个美国的一个缩影,现在,这些已经导致越来越多的孩子们,无论种族,也无论性别,正在被拒之于美国梦的大门外。
既然我们要探讨机会平等,1959年的克林顿港就是开启我们本书旅程的绝好起点,因为它总是可以让我们警醒,美国梦已经同今天的社会渐行渐远了。
1959年6月1日,镇中心的克林顿港高中。暮色降临时,白昼的骄阳暑热渐已散去,夜晚的空气清凉如水。150名新科高中毕业生走下学校的阶梯,手中紧握着我们崭新的毕业证,毕业典礼刚过,大家同学少年,风华正茂。
在这个伊利湖畔欢乐友好的市镇(人口6500,大多数是白人),我们度过了美好的少年时光,虽然还对过去的生活眷恋不舍,但我们更对未来的前途信心百倍。一如既往,这是一场全镇范围内的庆典,1150人参加了我们的毕业礼。无论是否血脉相连,镇民们都把这群毕业生视作“我们的孩子”(our kids)。

唐
唐说起话来柔声细语,是一个来自工人阶级家庭的白人孩子,但我们班级中从来没人会在意他的家庭,因为唐是我们最闪耀的四分卫明星。唐的爸爸只受过初中教育。为了维持家庭的生计,这位父亲不得不起早贪黑,打两份工——第一份工作是在克林顿港制造工厂的流水线上,从早晨七点开始,到下午三点结束;第二份工作是步行至不远处的一家当地罐头厂,工作从三点半开始,一直要干到晚上十一点。
唐的妈妈念到了高中二年级,用唐的话来说,她就“活在厨房之中”,整日操心着全家人的一日三餐。每天晚上,这位妈妈都会和唐以及他的两个兄弟坐下来一起吃饭。他们吃的通常是零碎食物,把厨房里所有能吃的东西配上土豆一起油炸。等到他们的父亲下班回到家时,男孩们早已进入梦乡。
唐这一家人住在镇上较穷的区,一直到唐离家上大学时,他们家都没有汽车,连电视也没有。要知道,当时美国80%的家庭都有一部汽车,90%的家庭有一台电视。每周去教堂的时候,他们的邻居会将唐家人带上。他们没有钱外出休假旅游。不过,他们住在父母有其产权的房屋里,因此感觉到经济上尚且安全。唐回忆道:“我从来不知道自己是个穷孩子,直到我上了大学,修了《经济学入门》这门课,我才发现自己一直是‘被剥夺的’(deprived)。”
虽然家境平平,唐的父母还是敦促他一定要上大学,如同我们班里许多工人阶级家庭的孩子,唐选修了克林顿港高中的大学预科课程。他的母亲逼着他练了六年的钢琴,但他的真爱却是体育运动。唐是篮球和橄榄球赛场上的健将,即便工作再忙,他的父亲也绝不会错过他的每一场比赛。
在接受我们的访谈时,唐轻描淡写地带过了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他说道:“我家住在镇东边,有钱人住在镇西边。但大家相逢在运动场上,每个人都是平等的。”
尽管唐的高中好友无一人进入大学,但唐自己的学习表现却十分优秀,毕业时成绩位列我们全班的前四分之一。据他所言,他的父母对大学“一无所知”,不过幸运的是,他在教会里有熟人。“镇上有位牧师一直很关照我”,唐说道,“他还向我最终就读的大学推荐了我。”不止如此,在申请助学金以及整个录取过程中,这位牧师也对唐多有指点。
从克林顿港高中毕业后,唐升入俄亥俄州南部的一所教会附属大学,在这里,他仍活跃在橄榄球赛场上,随后进入神学院。据唐所言,在读神学院时,他曾一度怀疑,他能否“如赛场上那般游刃有余地”做个牧师,于是他回到镇上,准备告诉父母他要退学。回家那天,唐路过镇上的台球房,顺道跟老板打声招呼。这家店的老板是他父亲的老朋友,见他前来,便把他隆重引见给店里的客人,称唐是“咱们未来的牧师”,还有一位客人请唐为他祈祷——他不由感到,这些迹象表明,自己应当继续牧师的人生之路。
大学毕业后不久,唐就和一位名叫琼的高中老师结婚了,他们婚后育有一子,这个孩子后来成为一所高中的图书管理员。在度过了多年成功的牧师生涯后,唐最近才刚退休。但他仍不时到镇上的教堂帮个人手,而且多年来一直执教高中的橄榄球队。回顾往事,他说自己这辈子得到了上天的眷顾。唐出身于一个贫穷但却友睦的家庭,却能成为一名成功的职业牧师,这反映出他与生俱来的才能和球场上的不屈勇气。但也正如我们所能看到的,唐所取得的这种社会上行流动(upward mobility),在我们那个班级中并不是个案。
弗兰克
弗兰克来自克林顿港少有的富庶家族。自19世纪末,他的外曾祖父就开始经营渔业生意,到弗兰克出生时,他的家族企业已经是多元经营,不但进入房地产业,还将触手伸入当地多家商业机构。早在20世纪30年代,弗兰克的母亲就从大学毕业,紧接着还在芝加哥大学取得了硕士学位。弗兰克的父亲是一位受过大学教育的牧师之子,就是在芝加哥,两人相遇,很快结为夫妇。弗兰克出生后,他的父亲开始接管家族的生意——渔业、农场、一家购物中心,还有镇上的餐厅等——而他的母亲则投身慈善事业。
克林顿港有一家游艇俱乐部,向来都是当地社会精英的会所。在弗兰克还是个孩子时,他的外祖父、父亲和舅父就已先后担任过游艇俱乐部的“会长”,而他的母亲和姨母则被选为“船长”——已然臻至当地社会的金字塔顶峰。一言以蔽之,在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同学的家长中,弗兰克的父母最有钱,受教育程度最高,社会声望也最为卓著。
同弗兰克的家庭相比,那些处在社会经济底层的家庭差的可不是一点半点,但即便如此,如果较之于今日美国(甚至是克林顿港)普通存在的两极分化,50年代的社会差距还是要缓和得多。弗兰克的家,同唐的家相距只有四个街区,在他的记忆中,邻里可以说是“各色人等的美妙杂居”——卡车司机、杂货店店主、环洋超市的收银员、本地公司的员工、消防队长、加油站老板、护猎员。“我们不是一起在后院打棒球,就是在街角踢足球,”弗兰克回忆起往事,“人与人之间相处,和谐融洽。”
尽管家世殷富,但从15岁那年开始,弗兰克就在家族经营的餐厅里打暑期工。同他的高中伙伴们一起清除涂鸦,打扫卫生。他的家族谨慎低调地处理他们的社会地位。“当你身在克林顿港,周围的孩子们都只买得起一罐可乐,那你也只能买可乐,”记忆中,弗兰克的外祖父就曾这样训斥过他的舅父,“如果我们到了克利夫兰或纽约,你想买什么,就买什么,但是当你和克林顿港的孩子们生活在一起,你就绝对不能出格。”
读高中时,弗兰克完全融入到班集体,和同学们打成一片——他行事低调,这让很多同学以为他就是一个寻常百姓家的孩子。不过,蛛丝马迹仍有显现。弗兰克是我们班第一个带牙箍的孩子。上小学时,每到冬季,他就有几个月在位于佛罗里达的家族别墅里度过,在那里上学。他的外祖父是我们学校的校董。曾有一次,弗兰克的父母邀请了一位老师来家共进晚餐。事后,弗兰克还责怪他的母亲,“你这么做,分明是要让我在全班同学面前难堪!”还有一次,父母有意出面干预他一门课的成绩,这让弗兰克感觉岂有此理:“你们是在开玩笑吗?天呐,在我们孩子眼里,老师永远都是对的。”
论学习,弗兰克资质平平,但这并不意味着父母会放松对他的教育。“从出生那一刻直到进入大学,我的人生早已被规划好了,”弗兰克告诉我们,“我知道自己得上大学,最好还要坚持到毕业。”在父母的经济资助下,他进入了本州的一所小学院,主修新闻专业。大学毕业后,他参加了海军,入伍七年的时间,他驾驶着海军运输机在全世界环游。“我爱那段日子!”弗兰克回忆道。
海军退役后,弗兰克在《哥伦布邮讯报》做编辑,一干就是25年,最终却因为反对社里一些人事变动而被炒了鱿鱼。从那以后,他重回克林顿港,半退休地在家族企业里做事,先后做过鱼类清洁、码头租赁,还经营过时装店。世事艰难时,靠着外祖父在他出生时就设立的一份信托基金,弗兰克还可以安然度日。“不是什么大钱,”他说,“但至少我不会挨饿受冻。”弗兰克的家族财富就这样保护着他,使他不致因生活的碰壁而伤痕累累,但这份财富又绝非那种可以助他一飞冲天的跳板,让他可以遥遥领先于唐以及普通人家的同龄人。
50年代克林顿港的阶级差异
回到20世纪50年代的克林顿港,阶级差异并不是消失不见,但如果说弗兰克和唐的人生故事告诉我们什么,那就是这种阶级差异还是隐而不彰的。
体力劳动者的孩子,同职业人士的孩子生活在相似的家庭环境中,从校园和邻里社区,到童子军和教会团体,两类家庭的孩子们自然而然地打成一片。现如今,无论是经济安全、家庭结构和养儿育女,还是在学校教育和邻里社区内,阶级差异都表现得壁垒分明(正如我们很快就可发现,即便在克林顿港也是如此),而回到50年代,阶级差异如果说有的话,也是微不足道的。如果我们看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的毕业生,无论家庭背景如何,几乎每一个孩子都成长于完整的家庭中,生活在自家拥有的房产里,邻里之间友爱团结。
我们的父母文化水平都不高,通常是母亲居内持家,父亲在外赚钱养家。事实上,在我们的父母中,大学毕业的比例尚且不到5%,1/3的父母甚至连高中也不曾读完。(在高中教育普及之前,他们中的大多数就已经结束了自己的学业。)但是,镇上每个人都得益于二战后美国普遍的经济繁荣,只有屈指可数的家庭才受过贫困之苦。而如弗兰克这样来自富裕家族的孩子在镇上可谓是凤毛麟角,而即便是他们,也在尽己所能地隐藏着这个事实。
有些人的父亲干体力活,忙碌在当地汽车零件厂的流水线、市镇周边的石膏矿场、本地的陆军基地或者小型家庭农场。还有些父亲是小生意人,比如我的父亲,财富随着商业周期的波动而起起落落。那个年代,一个勤劳的人不愁没工作,工会组织也强健有力,很少有家庭会遭遇失业或严重的经济困境。同学们无论社会出身,大都热情地参与运动、音乐、戏剧,以及各类的课外活动。每逢周五晚的橄榄球比赛,镇上的人们总是如潮涌到球场。
半个世纪后,回首过去,我这一届同学(多数现已退休)活出了精彩的人生故事。在我们中间,近3/4的同学的受教育程度要高于他们的父母,绝大多数在社会经济的阶梯上攀登得比父辈更高。事实上,那个时代出身平平的孩子,时常反而比家境优渥、父母受过高水平教育的孩子取得更高的社会经济成就。若是以当代的标准来看,我们班同学在教育上的流动程度尤其引人注目,这当然折射出20世纪高中和大学教育革命的杰出成就。
当年高中辍学的父母们,他们的子女过半数上了大学。在这些孩子中,很多不但是家庭里的第一位大学毕业生,甚至还是完成高中学业的第一人——短短一代人的时间就完成了如此进步,实在是非凡的成就。更令人鼓舞的是我们班上两位仅有的黑人孩子的人生故事,如下文所见,虽然他们要同种族偏见做斗争,虽然他们的父母无一从小学毕业,但这两个孩子还是获得了硕士学位。
回到50年代的克林顿港,无论何种肤色或种族的孩子,社会经济意义上的阶级都没有构成如此不可逾越的障碍,但到了21世纪,阶级就成为了一座新的大山。如果平均而言,1959年那一届学生的孩子并没有取得超越他们父辈的任何教育进步。8这就好像曾有一道自动扶梯带着1959届的大多数学生向高处走,但就在我们自己的子女行将踏上之际,这扶梯却戛然而止。
就我所在的1959届毕业生而言,如果每个人前进的步伐一致,就会出现绝对社会流动高,但相对社会流动低的情况。但实际上,在我的同学中间,即便是相对社会流动也是很高的。如果我们考察来自社会经济下层家庭的孩子,就会发现,他们所取得的上升流动并不亚于那些出身最优越的孩子。简言之,为数众多的底层孩子大踏步地向高处走,而顶层的孩子则有少数不进则退,甚至是退步。
诚然,父母若是教育程度低,则他们的文化视野会更狭窄,对高等教育也所知甚少,对孩子教育的期望值经常也更低。然而,在50年代,只要有人鼓励我们读大学,我们就总是会读,无论这样的鼓励来自我们的父母,还是我们的老师、邻里社区的长者(比如唐所遇到的那位牧师),或者我们的朋友——在我们这代人读大学这件事上,经济条件、财务状况和居住社区环境并没有产生什么可见的影响。
在当时俄亥俄州的全境内,公私学校收费皆低廉,而且学生也能得到大量取自于地方,也用之于地方的奖学金——扶轮社(Rotary Club)、汽车工人联合工会、青年妇女俱乐部等。如果统计克林顿港高中1959届学生中的全部大学毕业生,其中2/3是其家庭中第一个读大学的,1/3甚至是家庭中首位完成高中学业的。
当60年代的序幕在克林顿港缓缓拉开之时,一项温和的教育改革也随之到来,新举措针对来自贫困家庭的优异学生,旨在为他们提供更好的学业指导。种种迹象表明,机会平等时代的钟声已经敲响,但正如我们在本书中所能读到的,也正是在那个时刻,美国的社会历史发生了路线的逆转。
有些出身中下层阶级的孩子,高中毕业后并未立即进入大学,他们中间约有1/3的最终曲线救国,通过诸如社区大学这类机构完成了高等教育,而且在这部分同学中间,更卑微的家庭出身并未造成进一步求学的逆境。他们的成功或许姗姗来迟,但只要是成功,还是更进一步地弱化了在家庭出身和最终教育水平之间的关联度。
统计我在克林顿港高中的同学,相关证据可以毫无疑义地表明,克林顿港在50年代是一块社会流动取得超凡表现的乐土。经济贫困、家庭破碎、邻里淡漠、贫富两极分化,以及社会组织涣散,在今天看来,上述因素强有力地决定了社会经济地位的代际延续,但在20世纪50年代,它们都是微不足道的,上一代的社会经济地位并不会直接传递给下一代,也正是因此,社会流动远高于今天。
一次又一次地,1959届的同学们会用一样的话来形容我们青年时的物质生活条件:“我们很穷,但是我们并不知道什么是穷。”事实上,如果要看我们那代人所曾享有的宽广而深厚的社区支持,我们是富有的,但同样是我们并未意识到这一点罢了。
【作者简介】
罗伯特·帕特南,1941年生,美国当代最杰出的政治学家,曾担任美国政治学协会主席。哈佛大学马尔金公共政策讲席教授,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士,2006年荣获政治学界最高奖约翰·斯凯特奖,且为2013年总统颁布的国家人文勋章得主。曾出任肯尼迪政府管理学院院长。目前著书14部,被译为20多种语言,在比较政治、美国政治、国际关系和政治理论领域均做出过卓越的原创贡献。代表作《让民主运转起来》和《独自打保龄》是过去半个世纪引证最多的社会科学著作,在国内学界和思想界也有深远的影响。多年来,他担任过多届美国总统、英国首相、法国总统以及多个国家政府首脑的资深顾问,其学术思想也激发了全球范围内草根社会运动的勃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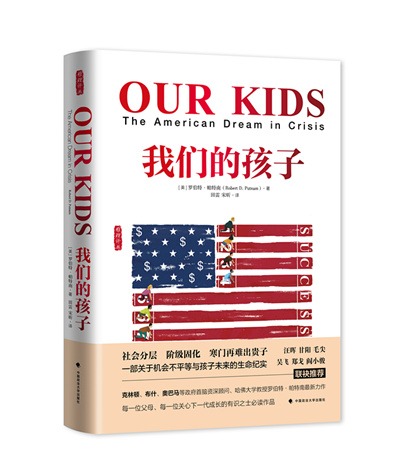
*本文节选自《我们的孩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2017年5月出版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邱铭珊)
(来源: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