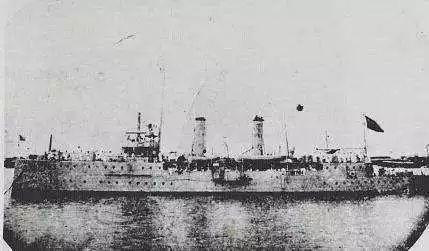
1926年3月19日夜,文德楼李宅响起重重的敲门声,李之龙与新婚妻子潘慧勤从梦中惊醒。女佣开门后,军人们冲进来,李走出睡房,见到六七个腰挎驳壳枪的士兵。“你们想干什么?”李之龙喝道。虎门要塞司令陈肇英冷冷地说:“校长命令,立即逮捕你!”五花大绑的李之龙被押上一辆无蓬大卡车,从文德东路转经万福路一警岗时,在枪杆子的簇拥中李大叫:“拉生啊!我是海军局长,他们是匪徒,半夜三更捉人,救人啊!”立即引来车上第一军士兵的詈骂:“X你老母!嚷什么!不要命了!”
劫后家中,哀哀哭泣,梨花带雨的潘慧勤心里一个念头闪过,连泪水都顾不上擦拭,冲出大门,来到此楼的3号二楼门前,急促地敲打着木门……

文德楼,建于1925年。5幢3层鲜亮鹅黄色楼房连成一体,位于广州文德东路文德里。 文德路有四十余处旧书摊和古玩店,文华阁、萃经堂等字号名传遐迩,成为古玩字画一条街。这年秋,中共广东区委军委租下此楼部分房屋。时任中共广东区委常委、军委书记的周恩来,与邓颖超住文德楼3号二楼[在此成婚];李富春、蔡畅夫妇住1号二楼;李之龙住4号二楼。天井里有几株翠绿的龙眼树,枝叶间一簇簇黄白色花朵开得繁盛。
门打开了,潘慧勤风一般冲进屋,她要将事变第一时间报告周恩来、邓颖超……
中共党员李之龙,黄埔一期。黄埔军校是国共两军将帅(帅仅指我军)摇篮,将帅不将帅,日后还要看各人的才华、功勋和际遇。此时,他的同期或后期同学许多还是尉官,他却已是海军中将、海军政治部主任、海军局代局长。广州革命政府海军未设舰队、司令,局长为最高军事首长,指挥各舰。在校时,他就是风云人物。在第一次东征时立有战功。他原是鲍罗廷的英文翻译,受党的指派投考黄埔军校。
17日上午,从黄埔军校传来了谣言:“共产党策动海军局的中山舰密谋发动武装政变。"次日下午中山舰果然准备开往黄埔。国民党宣传部代理部长毛泽东问过李之龙。李回答:“这是校长(蒋介石)的命令。”
本来国民党二次全国代表大会以后,市内谣言很多。后来据报第一军第二师师长王柏龄部队内也流传这个武装政变的谣言,而王柏龄不但不查禁,反而在对部队的连长以上各级军官训话时要他们枕戈待旦,扑灭共产党的阴谋。王柏龄师驻广州城内,他的训话由第二师的士兵传到全市,人心开始不安。

广东咨议局旧址,位于大东路(今中山三路)。主楼建筑为圆形的两层高的砖木结构楼房──古罗马式议会建筑,主楼为前圆后方的两层楼。去年11月,国共合作大本营──国民党中央党部由越秀南路惠州会馆迁到这里办公,国共两党代表参加的最高政治决策机关政治委员会也在这幢房子后座的原粤军总司令部楼上办公。
 钱币上的广东咨议局
钱币上的广东咨议局
月晕而风,础润而雨。毛泽东见微知著,预感到要出事了。
19日下午,三十二岁的毛泽东一身粗布衣,脚穿黑布鞋,从国民党中央党部二楼宣传部办公室走出来,穿过弧形联拱式的门廊──正中有四石柱,直顶楼檐。步下石階,走过荷花池上石拱桥,池中荷叶田田。“怕是见不到这里的荷花开了。”他想。直出大门,便是大东路,进入越秀中路,路边骑楼石柱或水泥柱上,贴着标语“工人农民联合起来!”“打倒帝国主义!”“打倒封建军阀!”“废除一切不平等条约!”和宣传画──衣衫褴褛、手执镰刀斧头的工农怒气冲冲在冲锋,前方地上是逃窜者丢弃的高筒大礼帽,白毛帚军帽和瓜皮帽。右转进入文明路,不用半个小时,就到达文远楼。

中共广东区委(当时也称粤区委)又称两广区委,是全国五大区委之一。它的管辖范围,除广东、广西外,到今年初还扩展到福建西部、南部、云南以及南洋一带。1927年,广东全省党员达九千多人,占全国党员总数的六分之一,其中广州就有党员两千多人。广州的三十多个党支部统一由广东区委直接领导。“管东渠”(“广东区”的谐音)为广东区委代号,此化名原为向警察局登记租赁房屋文远楼──位于文明路南的一座四栋三层相连的民国初年坐南朝北骑楼建筑,为区委机关驻地。一楼临街是糖水铺、鞋店、中草药铺等。最西边那幢。二层楼上东边为区委办公地方。
此时,毛泽东在区委领导之下(他并非中共中央委员或候补委员,毛还是国民党中执委候补委员。在国民党内职务高过共产党内。他似应属中央党部中共支部。)
熟门熟路,上得狭窄、陡峭楼梯,二楼外边一厅,一张旧餐桌,周围是高高低低的椅子和长长短短的板凳。既是会客厅,又是会议厅,还是歺厅。毛泽东向一位熟悉的工作人员点头微笑,举起右手上指,该传达会意地笑说,毛部长,陈书记在呢。

三楼北面,陈延年办公室,也是卧室。用木板与秘书处隔开,屋内空荡荡的,一个贴墙而立的大书架。东面墙上挂有马克思、列宁画像,挂着中国地图和世界地图,南边门角放着一个报纸架,靠南边窗口左角还有一张小茶几,上面放着一部西门子手摇电话机和一套石湾茶具。窗子对面床上铺着粗布蓝床单,打着补丁。靠窗条桌上,摆满文件和书本,几个白木方凳,一把破旧藤椅上坐着一个中等个子、穿浅蓝色粗布学生装、二十八岁的年轻人,正伏案写着什么。延年自幼身体壮实,皮肤粗糙黝黑,性格内向,脾气像父亲陈独秀一样倔强,平时沉默寡言,虽曾留法、留苏,粗手大脚,看上去不像个读书人 ,家中人称他为“黑面武生”。
一进门,毛泽东就说:“延年,你好!”
转身回首,陈延年立刻站起来:“润之,你好啊!我刚从上海回来,”说着就沏茶、倒茶,双手奉上:“请品尝下瓜片,才捎来的家乡茶。”
毛泽东呷了一口,甘醇满颊。“这茶平时喝得不多,绿茶里是很好的。延年,风起于青萍之末,侵淫溪谷……‘共产党要政变’的谣言越传越猛了。什么人在暗地里推动,这时候,我们要警惕啊。”
“润之说的对。”
说话的是刚进门、瘦瘦的戴眼镜的青年,浓浓广东口音的官话;他是隔壁办公的区委常委、区农民运动委员会书记阮啸仙,把手里的文件向陈一递,“今年一月起,我省有组织的农军就有三万人了。要好好锻造。一旦有事,才靠得住。”
“广东有五十万之众的农会会员,他们支援五卅运动,省港大罢工,二次东征,立下了汗马功劳。省港罢工委员会工人纠察队三千人,省港罢工在穗工人就有几十万,可惜,我党没有一支自己的武装力量,只有叶挺独立团尚可掌控。”毛泽东说。
“你们所言甚是。 只是事出有因,查无实据,只能提高警惕,静观其变。区委要睁大眼睛,竖起耳朵,打醒精神。别人都扬言要“枕戈待旦”了么。其实,不是什么“枕戈”,而是磨刀霍霍,取的是攻势。我们不能睡在鼓里!”
同日晚上,毛泽东和沈雁冰(毛部长秘书、此时尚未启用笔名茅盾)在家里谈起这些事,皱着眉头说,莫非再出个廖仲恺事件。
昨天,毛泽东在《纪念巴黎公社的重要意义》的演讲中说:“各同志要鉴往知来,惩前毖后,千万不要忘记‘我们不给敌人以致命的打击,敌人便给我们以致命的打击’这句话。”
深夜十一点半钟光景,该部图书馆的一名杂役,慌慌张张来到东山庙前西街38号,敲了敲这家的木门,应门的是女仆。
东山是别墅区,有成片豪华的洋楼。蒋介石就住在这里一所洋楼里,俄国军事专家顾问团也住在附近的洋楼里。庙前西街38号却是一栋简陋的二层唐楼。毛泽东和夫人杨开慧偕子英、青住在楼上,楼上大小三间,外面一间是会客室,里面一间是卧室兼书房。楼下也是前后两间,后面一间是厨房和保姆的卧室,楼下住着肖楚女、沈雁冰。
当时,肖未在,毛和沈都还没有睡,坐在楼下门厅藤椅上谈论广州的形势。毛说:鲍罗廷回国了,加伦将军也回国了,代理苏联军事顾问团长的季山嘉对广州各军情况不了解。
正说到这里,工友进门,看见毛泽东,就用广东腔半生不熟的官话说,李之龙刚才被捕了!
毛泽东说:现在是查有实据了。他吩咐那个工友去找陈延年。毛默然沉思,显然是在考虑问题。沈不敢打扰,也默坐相陪。
楼上,杨开慧给岸青喂奶后,母子三人早已睡熟了。
那个工友终于回来了,他说街上已戒严,但夜市大排档未收市,士兵们在赶走逛夜市的人,十分混乱,他没有受到盘问。对于那里鸡飞狗跳情形绘声绘色的冗长描述,毛泽东予以打断,问道,陈延年同志呢,见到没有?工友说,他在文德楼附近看见他带着他的秘书,据秘书说,是前往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宿舍。于是毛泽东不再多问,挥手叫他回去睡觉,对沈说:我现在去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沈说:“路上已戒严,恐不安全,我陪你去。"毛泽东点头同意。
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离毛寓所不远,路上无异常。但到达时,却见士兵甚多,简直把宿舍包围起来了。毛沈走到宿舍大门前,就有两个士兵上前盘问。毛泽东答道:“我是中央委员、宣传部长。”又指着沈说:“这是我的秘书。"士兵听说是中央委员,就陪笑道,请进。进了大门,是个传达室,毛叫沈留在传达室,独自走进里面的会议室。陈延年已在那里。
陈说,蒋介石不仅逮捕了李之龙,还把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统统逮捕,关在一间大厅里,扬言第一军驱逐共产党员。这是突然袭击,事态严重。
苏联军事顾问代表团的代理团长季山嘉说,蒋介石还要赶走我们苏联军事顾问团。这还了得!
毛泽东心中怒火像地层深处的熔岩涌动,辞锋如刀劍锐利,议论如江河浩荡:“这几天我都在思考。我们对蒋介石要强硬。蒋介石本来是陈其美的部下,虽然在日本学过一点军事,却在上海进交易所当经纪人搞投机,当时戴季陶和蒋介石是一伙,穿的是连裆裤子。蒋介石此番也是投机。我们示弱,他就得步进步;我们强硬,他就缩回去。”
“我们应当动员所有在广州的国民党中央执、监委员,秘密到肇庆集中,驻防肇庆的是叶挺的独立团。目前就广州一隅而言,蒋介石的武力占优势,他有王柏龄一个师的兵力,再加上吴铁城手下的武装警察,就有一个师和一个营了。然而就两广而言,蒋介石这点兵力就居于劣势。第一军的士兵和中下级军官都是要革命的,蒋介石的反革命面目一旦暴露,第一军就会反对他。况且,第二军谭延闿,第三军朱培德,第四军李济深,第五军李福林,都与蒋介石面和心不和,李济深与蒋还有宿怨。二大以后的新中央执委会,又升蒋介石为军事总监,平空在各军之上又来一个人管制他们,他们更加不服气。因此,我们可以争取他们,至少可以使他们中立。
中央执、监委员到了肇庆以后,就开会通电讨蒋,指责他违犯党纪国法,必须严办,削其兵权,开除党籍。广西的军事首领李宗仁本来和蒋有矛盾,加上李济深,这两股力量很大,可能为我所用。摆好这阵势对付蒋,蒋便无能为力。”
祸起萧墙,仓促之间,怎么办?这是一个行动方案。
陈延年先是站在毛一边,可是,以季山嘉为首的苏联军事代表团却反对。认为真要打仗,肇庆一地的财力要支付一个独立团的费用,必然不够;而广州的税收比肇庆多十倍。即使其他各军都袖手旁观,蒋介石有一个师的兵力加上吴铁城的武装警察,对付独立团就绰绰有余。况且独立团只有手头的弹药,无法补充,而蒋介石刚收到苏联运来的大批弹药。就这点而言,独立团不能坚持到一个星期。
季山嘉这样一反对,陈延年也犹豫起来。毛泽东再三跟他们理论,没有效果; 陈虽然同意毛泽东的见解,但他也说自己“不敢做主”,要“请示上海中央”才能决定。
沈在传达室先听得讲话的声音,像是毛泽东的。后来是多人讲话的声音,最后是高声争吵,其中有毛的声音。又过一会儿,毛泽东出来了,满脸怒容。他们回到家中门厅坐定,毛泽东脸色平静了。应询给沈讲了会谈大致情况。
沈问:“您料想结果如何?”
毛泽东思索一会儿说:“这要看中央的决策如何,如决定对蒋让步,最好的结果大概是第一军中的共产党员要全部撤走了。重要之点不在此,在于蒋介石从此更加趾高气扬,在于国民党右派会加强活动,对我们挑衅。”
此时已过午夜,毛说:睡觉去罢。就上楼去了。沈在床上却辗转不能熟睡,但听不到枪声,料想没事,也就睡着了。
总书记陈独秀与中共中央机关此时均在上海,对事变最先是从上海报纸的新闻通讯获悉的。各报大字标题:“中山舰图谋不轨”,“蒋介石扣俄顾问”,“逮捕共产党”,“解散省港罢工委员会”。“中共中央最初是不相信的,认为又是帝国主义者造谣。”( 张国焘:《我的回忆》)省港罢工后,我党同帝国主义国家的矛盾更加尖锐。它们认定中共是中国境内最坚定的反帝力量,只是还十分弱小。三月底,布勃诺夫使团回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他们那里得悉一些较为可靠消息,但不知道详情。”(彭述之:《评张国焘的〈我的回忆〉》)迟至4月中旬,中共中央才收到陈延年的详细报告。
我党尚无秘密电台,人送或邮局传递信息很慢。要求中央及时做出应变决策是不可能的。这样一个关系到国共合作全局、统一战线成败的大事由地方党委决策,陈延年心理压力自然很大:中共是共产国际一个支部,管东渠算是党小组吧。我这个小组长授权有限。
包惠僧回忆,当天上午(20日),周恩来到蒋发动事变的指挥部和扣押共产党员的场所──广东造币厂,当面质问蒋并斥责他制造反革命事件,破坏国共合作,无理扣押共产党人的罪行,迫使蒋介石不得不下令释放被扣押人员。
同日,陈延年、张太雷、恽代英召集了党员积极分子会议,说明事件事实真相,揭露蒋介石反共、破坏国共合作的阴谋,号召大家提高警惕,加强工农武装队伍的建设,迎接新的斗争。
3月21日和30日,广东区委两次在《广州民国日报》上发表公开信,驳斥帝国主义与反动派对共产党的种种造谣污蔑,揭露他们通过反共达到破坏“联合战线”的阴谋。
高第街,离街口不远,一处高宅深院。门框两边挂着油得光溜溜、几尺长的白底黑字新木牌──军长谭延闿的颜体正楷楷书:东边,国民革命军第二军军部;西边, 国民革命军第二军特别党部。第一次来时,毛泽东见大门口这位同乡老熟人、前清翰林漂亮的手书(那时写的是湘军),贊赏地点点头:“不愧民国第一颜!”。
一九二零年,毛泽东等在长沙创办“文化书社”,上门求字,请时任湖南督军、湘军总司令的谭延闿为其题写招牌。人称水晶球的谭虽不认识眼前这个年轻人,为人一向圆滑,还是为其题了字,并亲临为文化书社开业剪彩。此社后来成为湖南共产主义小组的秘密联络机关。
十年后,谭延闿在南京担任国民政府行政院长,当他从报纸上看到朱毛红军大举进攻长沙的消息时,懊恼得跌足叹息:“这个毛泽东,早知如此,当年我去剪什么鬼彩呀,派两个兵把他一捉,何至于今日劳师糜饷?”
这天,毛泽东走进这个大院,顾不上照例欣赏门框法书,心无旁骛,排闼直入第二军副党代表李富春家,正好碰上第一军副党代表兼政治部主任周恩来。周恩来后来回忆说:“我在富春家遇毛,毛问各军力量,主张反击。……我听了毛的话找季山嘉,他说不能破裂。”[《周恩来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的发言》1943年11月27日。]
当时,毛泽东、周恩来、陈延年、李富春等对情况的分析是:黄埔军校有五百多共产党员,在广东的国民革命军六个军中,五个军的军长和蒋介石有矛盾,而蒋的第一军中政治骨干大部分是共产党员,我们还掌握了一个叶挺独立团,从力量上看是可以反击的。只要我们态度强硬,国民党左派也会支持我们。
周恩来找到张太雷,要他向苏联顾问反映。此时苏联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正好在广州视察顾问团的工作,听到此事后,缺乏敏感,认为是大惊小怪,真正熟悉国民党内部情况的鲍罗廷、加伦此时又不在。周恩来十分焦急,却也无计可施。
陈延年有些心动,马上去找苏联顾问。可是苏联顾问计算了一下,认为叶挺部队只有一个团,武器弹药不足,难以与第一军抗衡。
与此同时,周恩来又找到季山嘉,主张出兵讨蒋。听完周恩来一番陈述,季山嘉面有难色。原来季山嘉也并非不知蒋介石的司马昭之心,早将此事汇报给正在广州访问的苏联代表团团长、红军总政治部主任布勃诺夫,布勃诺夫却要季山嘉劝说中国共产党切勿有过火行为。因此,季山嘉不仅没有同意周恩来关于武装反击蒋介石的计划,反倒说服周恩来不能与蒋介石公开决裂。
布勃诺夫知道,共产国际和苏共内部对中国革命的战略策略有两种意见。斯大林、布哈林等组成斯大林派,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组成新反对派。正所谓党内无派,千奇百怪。随着国共两党关系的变化,两派认识和主张的分歧越来越大。斯派力主维系现有统一战线形式,共产党人留在国民党内。新派则倾向共产党员退出国民党,实行党外合作或另组新党。
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托洛茨基、季诺维也夫、拉狄克等人提出了警惕以蒋介石为代表的国民党新右派叛变的警告。苏共视为对斯大林中国政策的攻击。布勃诺夫只能按照斯大林的指示处理中山舰事件。季山嘉也必须服从布勃诺夫。
二十日,街上已解严。沈雁冰到陈延年的办公地点,才知道蒋介石派兵包围苏联军事顾问团宿舍以外,还派兵包围了汪精卫住宅。蒋的部下对兵士说:共产党要造反,派兵去,是保护苏联顾问和国民政府主席。陈延年又说:蒋介石也包围了省港罢工委员会并收缴了纠察队的部分枪枝弹药(后又发还)。
中共中央在中山舰事件发生后,没有轻率决策,莫斯科方面迟迟没有消息。3月末,布勃诺夫等归国途经上海,中共中央才从布勃诺夫处得知有关情况。
过了两天,沈雁冰又见陈延年,问:事情如何结束?陈答:中央来了指示,要我们忍让,要继续团结蒋介石准备北伐。我们已经同意撤回了第一军中的所有党员。但蒋介石要求解雇季山嘉,这不是中国党内的事,让蒋介石自己向莫斯科办交涉。
4月3日,陈独秀发表文章,认为由于帝国主义和军阀的强大,中国的革命势力必须统一起来,文章宣称:“蒋介石是中国民族运动中的一块柱石”,共产党人决不会阴谋去推翻他。这篇文章是中山舰事件后中共党人的一个有权威性的表态,它实际上给中共应该做出的反应定了调。中共中央随即决定,“维持汪蒋合作的局面,继续对蒋采取友好的态度,并纠正广州同志们的一些拖延未解决的左倾错误”。同时,决定派张国焘赶赴广州,查明事实真相,执行这一妥协政策。
张国焘到广州后,立即召开广东区委紧急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妥协政策,要求一致遵行,他完全同意苏联顾问对蒋介石思想性格的分析以及“利用蒋介石”的策略。
然而,在张国焘离开上海之后,中共中央于4月中旬收到陈延年关于事件的报告,陈独秀看了怒不可遏。决定改变妥协、退让政策,采取一项新的政策,其要点为:尽力团结国民党左派,以便对抗并孤立蒋介石;在物质上和人力上加强国民革命军二、六两军及其他左派队伍,以便于必要时打击蒋介石;尽可能扩充叶挺的部队、省港罢工委员会指挥下的纠察队和各地的农民武装,使其成为革命的基本队伍,并决定在广州成立特别委员会,彭述之为书记。
4月末,彭述之受命前往广州,和鲍罗廷面商上述计划。彭述之到达广州后,即成立特委机关,召开会议,传达中共中央的新政策,结果,遭到刚刚回到广州的鲍罗廷的强烈反对。彭向鲍提出陈独秀把给蒋的军火中拿出五千支步枪给共产党用以武装广东农民,鲍却拒绝了。还说:“现在是共产党应为国民党做苦力的时代。”
可以看出,中山舰事件之后,在制订和执行对蒋妥协、退让政策的过程中,起重大作用的是共产国际和苏联方面,陈独秀和中共中央不应承担主要责任。成也国际,败也国际。
中山舰事件后,蒋介石食髓知味,打蛇随棍上。得垅望蜀,提出整理党务案来排挤共产党人,担任国民党中央部长的共产党员,组织部长谭平山、代理宣传部长毛泽东、农民部长林祖涵以及中央执行委员会秘书长刘芬等全被撤换。共产党员被扫地出门。从而加速了国共第一次合作的破裂。毛泽东“不见荷花开”一念成谶。从三二0事件到四一二事变,只有一年。
中山舰事件的最大教训是揭示了中共建立军队的极端重要性。斯大林说:“在中国,是武装的革命反对武装的反革命,这是中国革命的特点之一,也是中国革命的优点之一。”此话是至理名言,但他当时讲话的具体含义──“ 武装的革命”,指的是国民党领导的国民革命军,苏联为国民党运军火,办军校,派军事教官、顾问,对中共则不给军火,甚至连口头或书面指示都不涉及中共建立或领导革命军队。
那些日子里,被沈雁冰评为“十分恬静贤淑”的开慧数次听到夫君家中踱步时低声哼唱湘味京戏《击鼓骂曹》:“ 我有心替主爷把贼扫,手中缺少杀人的刀。”
参阅: 茅盾《我走过的道路(上)》 人民文学出版社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马达时。作者投稿。责任编辑:邱铭珊)
(作者:马达时。作者投稿。责任编辑:邱铭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