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图片来源:网络)
(图片来源:网络)
今天我要讲的题目是“中国之路:民族主义,还是社会主义?”表面上社会主义是到处都还看得见的一块招牌,但是,对于我们许多人的内心来说,已经是一个很陌生、很遥远的概念。几年前,钱理群老师说,“这二十年来我们思想界最重大的一个失误,就是我们对中国的社会主义思潮没有经过认真的清理和研究”。社会主义有着沉重的历史负担和可怕的现实陷阱,尤其是在中国这个“社会主义国家”,来谈论“社会主义遗产”,无疑是一种巨大的困境。黄纪苏说,许多人觉得一丝不挂的资本主义要比三点式的社会主义痛快实在。因此,我其实不怎么喜欢社会主义这个不怎么痛快实在的词。
在梁漱溟晚年口述《这个世界会好吗》这本书中,我读到,1980年,梁漱溟很乐观地认为,在全世界,社会主义会终结资本主义:“我认为很自然地要走入社会主义,资本主义要转入社会主义。”(第21页)在他的心中,“改革开放”不是“门户开放”。他说,“还是为了中国走社会主义这个大道路而要四个现代化,不能离开走社会主义道路的四个现代化。”(第161页)梁做这个口述的那一年,我正好进大学读书,中国的改革开放刚刚开始。那个时候,许多事情都有点“拨乱反正”的意思,因此,当我今天读到这本书的时候颇有感触。
“改革开放”30年,中国经历了5000年文明史上最剧烈的巨变。中国的社会、政治、经济结构和文化、道德都急剧地发生了深刻的变化。中国迅速地造成了最严重的地区和阶级分化。中国成为“世界工厂”,快速释放出了巨大的物质财富,但这些财富却被极少数人攫取。“改革开放”越来越像一场“零和博弈”:在少数人暴富的同时,最广大的社会群体沦为了“弱势群体”。用孙立平的说法,今天的中国是一个“断裂的社会”,一个“裸体为官”、没有责任的上层和一个被全面剥夺的下层。今天的中国,专制与自由同体,暴富与贫穷携手,乐观和悲观并存,希望与失望共生。我们同时看到国家的崛起和社会的崩溃。现在的中国也许最适合狄更斯在《双城记》的开头说的那句话:“这是最好的时代,这是最坏的时代。”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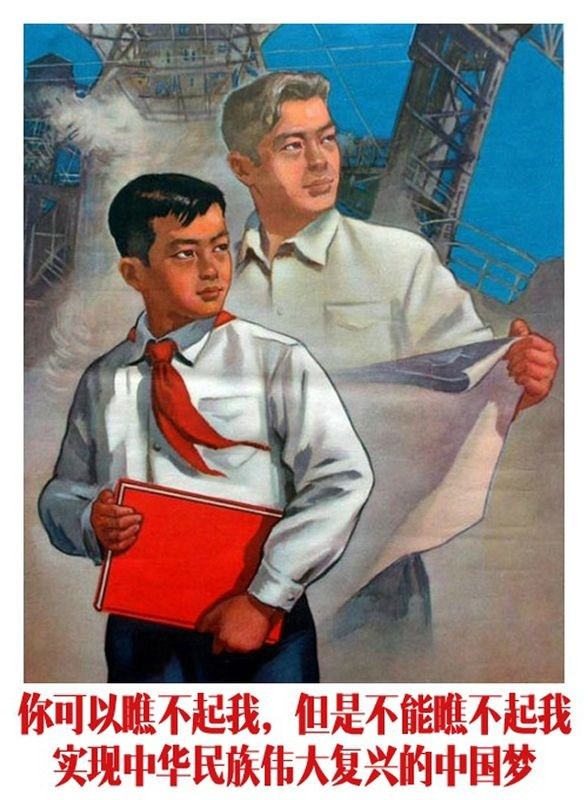
中国自上而下的“奉旨改革”,由于缺乏民众的参与,改革的过程也就是国家认同瓦解和社会分裂的过程。然而,需要明确的是,反思改革决不意味着应该回到文革。并且首先要提问的是,为什么会发生改革?改革的发生,是因文革失败了,文革的路走不通了。文革失败的终点成为了改革发生的起点。就像今天的改革一样,文革已经走到了它的尽头,到了天怨人怒的程度。用黄纪苏的话说,1976年天安门发生的反对“四人帮”的四五运动,就是人民对文革的公投。
2006年,中央电影台推出了被目为“新《河觞》”的电视政论片《大国崛起》,形成了“大国崛起”话语高潮。《河觞》和《大国崛起》是一部意识形态的连续剧。它们的区别,用李零的话说,只是一个是悲情版,一个是豪情版。今天,不论是官方,还是民间,也不论是在白天,还是在黑夜,我们都有“同一个梦想”,这就是“大国梦”。“大国”,翻译成五四时候的词语就是,“列强”。“大国崛起”的论述完全省略了资本主义、帝国主义列强崛起和殖民主义之间的历史联系。一夜之间,“资本主义列强”成为了“先进生产力”和“先进文化”的代表。“大国崛起”的论述是中国彻底脱离“第三世界”政治的一个明显标志。
中国会成为一个什么样的国家,在未来几年的时间里,能够给中国的发展提供什么样的思想和方案将会是非常重要的一个问题。最近几年,中国的政治表面上有一种左转的势头,但是,实质上却在急剧地右倾。同时,左翼思想进一步衰退。我发现一些左翼朋友迅速地转向民族主义和精英主义。一些人自称左派却不假思索地批判“普世价值”,盲目地搭上了民族主义便车。历史上任何进步的阶级和文化都自认为代表了普遍价值,《国际歌》就是以“英特纳雄耐尔就一定要实现”结束。当今这种民族主义转向并不是个人主观上的原因,而是因为历史条件的限制。左翼思想向民族主义退化,是中国思想萎缩和危机的一个重要症候。
同时,当我们在奢谈“大国崛起”的时候,全然忘记了在1991年之前,世界上曾经存在一个可以和美国平起平坐的“超级大国”苏联。与今天全球最大的买办国家不同,苏联不仅曾经拥有强大的政治、经济和军事力量,而且具有一套相对独立、完整的思想、文化和价值体系。苏联不仅最早爆炸了氢弹,而且率先把人造航空器送入了太空。我的许多左翼朋友说,中国应该造航母,发展军工。苏联的军事力量已经超过了美国,但是,这个“超级大国”却在一夜之间就崩溃了。
现在流行“软实力”的说法。尽管梁漱溟没有使用“软实力”这个名词,但他在1980年就意识到了“软实力”的存在。他认为,美国的上层建筑“很有力量”。他说,“现在上层建筑不单是一个掌权的问题,它也是学术文化,学术文化跟有钱、跟有权都连起来了,好象是不容易推翻的。”(第103页)当时,全世界将苏联看作是最强大危险的敌人,苏联不仅是和美国并列的超级大国,而且咄咄逼人有驾乎其上的趋势,美国和中国因此结盟抗苏。全世界几乎没有人预见到苏联的崩溃,但是,梁预言了苏联的崩溃。他说,苏联算不上什么社会主义,而是一种变态。他认为,苏联的这种党的专制不可能长久维持,会要起变化,这种统治维持不住了,没有力量维持下去,它要变化。(第102页)梁谈话后十年,1991年,苏联就崩溃了。
2007年是南京大屠杀70周年。我们怎么纪念南京大屠杀呢?我希望既不是简单的控诉,更不是在“盛世”的白日梦中陶醉和遗忘,而是痛彻的反省和思考:中国现代化到底还有怎样的选择和可能性?同时,我们怎样面对、思考南京大屠杀和中国现代史上的苦难?尤其是,这些绵绵不尽的苦难从来不缺乏堂皇的名义。
2007年,似乎是对南京大屠杀70周年的回馈,出产了《色·戒》、《集结号》、《苹果》和《投名状》等电影。这批大众文化产品受到了主流媒体的高调宣传和热烈追捧。它们成为了当年最有票房和影响力的电影。这批文化产品充分流露了这个时代的“集体无意识”。它们共同吹响了新意识形态的集结号,催生了一场具有深刻意义的“文化革命”。这场文化革命在2007年年底结晶成为一个流行的时髦词——“靠不住”:“看完《色戒》,发现女人靠不住;看完《苹果》,发现男人靠不住;看完《投名状》,发现兄弟靠不住;看完《集结号》,发现组织靠不住。只有靠自己了,我靠。”它体现了今天信任和共同体彻底崩溃瓦解的现实。
《色戒》激起了民族主义的强烈反应,引起了中国思想和知识界的激烈争论。《色戒》受到主流舆论的欢呼拥戴。我的朋友们尤其黄纪苏、祝东力和王小东对此很激动、很生气。黄纪苏义愤填膺、激昂慷慨:“中国已然站着,李安他们依然跪着”。可是,《色·戒》之所以引起激烈的争议,黄纪苏等先生们如此激动,如此敏感,其实就是因为中国还不够强大,还没有真正站立起来。
2008年,奥运火炬、藏独和汶川大地震激起了青年学生尤其是海外学子的爱国热情。学生们的爱国热情吓坏了吴稼祥先生,他在《中国青年报·冰点》上发表了《民粹一咳嗽 大众就发烧》的檄文,恨不能召喜马拉雅山冰川引太平洋之水来浇灭这群“爱国贼”的体温。
2009年,《中国不高兴》一书使民族主义再次处于媒体聚光灯的照射下。民族主义被自由派打成了“极左派”,真有点匪夷所思,因为在意识形态的光谱上,民族主义应该是位于右边的。从左派在《色戒》事件中为国民党和民族主义辩护到自由派将民族主义打成极左派,说明了今天中国思想界的极端混乱。
民族、阶级和性别是现代叙述的三个关键词。19世纪以来现代世界地图主要是由民族主义绘制的。民族国家是理解现代世界结构的关键。离开民族,我们就无法理解和把握现代世界。以民族国家为基本单位构筑起了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自然,当我们谈论民族主义的时候,是指政治民族主义。在现代历史上,中国的失败实际上是作为一个现代民族国家的失败。因此,中国现代历史的根本目的就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国民党为什么叫做国民党?顾名思义,国民党是一个民族主义政党。它的基本目标是要建立一个国民的国家。但是,国民党却没有完成中国民族主义的目标。在马克思的时代,欧洲无产阶级已经开展了共产主义运动和“阶级斗争”。但在马克思看来,被欧洲征服的亚洲和非洲,解放的第一步是首先要争取成为“民族”。因此,民族主义成为中国现代一个最重要的历史主题。(真能扯!)中国的资产阶级革命同时包括了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两方面的内容,而民族革命和民主革命实际上又是不可分割的。依照五四的说法是,我们必须“外抗强权,内惩国贼”,用王小东的说法是,“内修人权,外争国权”。民族主义构成了新时期一个重要的思想脉络。然而,新时期的一个根本转折就是,从社会主义转向民族主义。在目前,民族主义在中国所发挥的似乎是一种进步的作用。20世纪,许多知识分子和学生就是从民族主义的本能出发走向左翼的。但是,归根到底,民族主义是一种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特别是,今天中国的民族主义很容易被看作是美国霸权主义的简单盗版。而且,确实,今天“中美国”的说法,煽惑了中国精英们参与瓜分世界的幻想。
马克思主义认为,现代民族是人们在共同的生产方式、种族、语言和地域的基础上,通过长期稳定的经济联系而形成的社会共同体。资本主义造成了广大的市场,现代民族是伴随着资本主义生产关系的崛起而诞生的。然而,资本主义生产的性质,却又决定了民族无可避免地分裂为利益相对对立的两大阶级:资产阶级与无产阶级。尽管无产阶级构成民族的形式多数,但却始终处于被统治的地位。因为从根本上来说,民族国家建筑于阶级社会之上。因此,罗莎•卢森堡指出:“在阶级社会,民族作为浑然一体的社会-政治现象并不存在。任何一个社会生活领域(坚硬真实的物质基础也好,细腻复杂的精神生活也好)里,统治阶级和觉悟的无产阶级都不可能真正找到共同语言,更谈不上(在此前提下)构成一致对外天衣无缝的‘完整民族’”。[1]1920年,李大钊在《亚细亚青年的光明运动》中说:“日本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排日运动,我们固然不能承认;中华人说,中华的学生运动是爱国运动,我们也不能承认。我们爱日本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和爱自国或他国的劳工阶级、平民、青年一样诚挚,一样恳切。我们不觉得国家有什么可爱的道理,我们觉得为爱国去杀人生命,掠人土地,是强盗的行为,是背人道反理性的行为。我们只承认中华的学生运动,是反抗强权的运动。”[2]
在“大国梦”甚嚣尘上的时候,我想起1924年孙中山在《三民主义》的演讲中的警告:“中国古时常讲‘济溺扶倾’。……所以中国如果强盛起来,我们不但是要恢复民族的地位,还要对于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如果中国不能够担负这个责任,那么中国强盛了,对于世界便有大害,没有大利。”针对滔滔“大国梦”,最近,张承志在《三笠公园》中满怀忧虑地写道:“已经又是甲午年的天下大势。海水被舰首劈成两片白浪,他们队形严整,奏着进行曲驶过来了。而这一边却还没准备好——连民主都没有准备好。”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和民主,我们就不可能真正崛起;如果我们没有自由和民主,即使我们“崛起”了,也会是一种巨大的灾难:“由于失败的历史,新潮的大国梦变成了包围的众论,在一个世纪后一浪一浪地涌来。它崇洋的媚态,它专制的出身,它隐现的他者歧视,让我感觉紧张。” [3]在张承志看来,正确的取道应当是,我们必须侧身而立,“一面迎战着史无前例强大的帝国主义,同时批判着狭隘的民族主义”,“我们唯有在剧痛中,去追求彻底的人道主义。”[4]
本质上,现代民族国家是阶级国家,现代民族国家兴起的过程也是资产阶级作为一个新兴阶级登上世界历史舞台的过程。与此同时,现代民族主义动员的过程也是资本主义彻底扫荡封建主义的过程。作为西方入侵的产物和反抗帝国主义的武器,20世纪,中国的民族主义具有历史的合理性和进步性。无论国民党,还是共产党,其建党纲领都包含了反对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内容;但是,国共两党所寻求的力量却截然不同,国共两党民族建构的路线也绝然异径:国民党“五族共和”的中华民族定义,采取的是传统的“文化中国”的理解,而构成共产党意识形态的则是“阶级国家”。区别于西方资产阶级革命,GCD主张在工人和农民联合的基础上建立一种新型的现代民族国家——新民主主义国家。黄纪苏等人的中华主义论述之所以空洞虚幻、苍白无力,是因为他们没有认识到现代民族国家的阶级性质。如果民族主义是天经地义的话,那么无法解释这样一种悖论和荒谬现象:他们所谓的“汉奸电影”却受到主流的热烈追捧,相反,他们批判“汉奸电影”的言论却没有发表的空间。
国民党和共产党的出发点都是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其区别是以什么方式建立一个现代民族国家和建立一个什么样的现代民族国家。也就是说,以一种什么样的思路、方案来整合中国。这也就是毛泽东思想的内在逻辑。《毛泽东选集》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是1925年毛泽东作为国民党宣传部长时写的论文。这篇论文奠定了毛泽东思想的基础。这篇文章劈头就是我们非常熟悉的一句话:“谁是我们的敌人?谁是我们的朋友?这个问题是革命的首要问题。”那么,毛泽东怎样界定敌人和朋友呢?毛泽东的分析方法是从各个阶级与帝国主义的关系入手:“一切勾结帝国主义的军阀、官僚、买办阶级、大地主阶级以及附属于他们的一部分反动知识界,是我们的敌人。工业无产阶级是我们革命的领导力量。一切半无产阶级、小资产阶级,是我们最接近的朋友。”在这里,我们可以清楚地看到,毛泽东是依据什么来划分敌友和判别各个社会阶级的性格的。我们也可以看到,在毛泽东思想中,民族主义的目标怎样和阶级分析的方法结合在一起。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把民族主义划为了极右派:“地主阶级和买办阶级完全是国际资产阶级的附庸,其生存和发展,是附属于帝国主义的。特别是大地主阶级和大买办阶级,他们始终站在帝国主义一边,是极端的反革命派。其政治代表是国家主义派和国民党右派。”我们经常说蒋介石背叛革命,他背叛的是国民革命。毛泽东把他所领导的革命称为“新民主主义革命”,属于资产阶级革命的范畴。我们看到一个有意思的现象,当叶利钦说“民族和解”的时候,苏联解体,民族分裂。梁漱溟晚年有一个反省。他说,他曾经希望中国合起来,但中国没有合起来。毛泽东主张阶级斗争,结果却使中国合起来了。
今天,我们面临着想象力的失败,就像勃列日涅夫时代的苏联。这种想象力的失败将最终导致政治活力的消失和国家的崩溃。由于特定的世界格局,今天中国想象的空间极为有限,在所谓“历史终结”之后,今天甚至还不如1960年代当时两个阵营并存所提供的空隙。1990年代以来,我们批判乌托邦和理想主义,“现实”越来越强大,“理想”和想象失掉了自己的力量和位置。我感觉到,今天不论是所谓左派还是右派都面临着想象力失败的问题,都提不出真正有力的远景和方案,我们今天许多人在被历史拖着走。
当我们被历史拖着走的时候,应该回头看一看,看看过去的历史是怎么发生的。1979年“改革开放”,历史发生了重要的转折,历史地这里拐了一个弯。那么,“改革开放”的历史是怎样发生的呢?
1978年10月,邓小平访问新加坡时,答应李光耀提出的“中国必须停止革命输出”的要求,停止对东南亚的广播和对东南亚共产党的援助。
1978年7月,中美两国代表在北京开始建交谈判。1978年12月13日,邓小平在北京会见了美方谈判代表伍德科克,直接与他就建交联合公报方案交换意见,使中美建交谈判在数日内一锤定音。1978年12月16日,中美两国发表了建交公报,宣布自1979年1月1日起互相承认并建立外交关系。
1978年12月中共11届3中全会召开,标志着“改革开放”正式开始。
1978年11月西单出现大字报,为了向华国锋的“两个凡是”挑战,1978年11月26日,邓小平在接见日本社民党委员长时说:“写大字报是我国宪法允许的,我们没有权力否定批判群众发扬民主,贴大字报,群众有气就让他们出。”第二天,一个加拿大记者在西单民主墙传达了邓小平谈话的内容。[5]……
1979年12月6日,北京市规定,今后凡在自己所在单位以外张贴大字报,只准在月坛公园内的大字报张贴处。(《1979年12月6日 西单“民主墙”禁贴大字报》,《人民网》)“西单民主墙”由此消失。
1979年2月17日,中国与越南爆发边境战争。刘亚洲认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的第一步就是从这场战争中迈出去的。”他对中越战争有过这样的解释,他说中越战争是中国为美国人出气,是打给美国人看的:“小平同志前一天访问白宫出来,第二天就开打。为什么要为美国人出气?美国人刚刚灰头土脸地从越南走掉了。”“小平同志这个时候发起对越自卫还击作战,就是把自己、把中国从所谓的苏联社会主义阵营中划出来。当时许多东欧国家都不满意,说社会主义国家打社会主义国家。” [6]针对中越战争的后果,本尼迪克·安德森在《想象的共同体》第二版的序言里说,社会主义把信错误地送到了民族主义的手中。
1979年12月27日,苏联入侵阿富汗。随后,中国和西方联合抵制了1980年莫斯科奥运会。这是奥运史上第一次将奥运会政治化。
1979年5月3日,玛格丽特·撒切尔赢得英国大选。她宣布:“英国公民放弃了社会主义,30年的实验彻底失败了——他们准备尝试别的东西。”1980年11月4日,罗纳德·里根当选美国总统。撒切尔和里根强力推行新自由主义政策。他们的政策被称为里根-撒切尔主义,导致了全球的政治右转。
中国的“改革开放”不仅有内部的逻辑,同时,国内的小气候又是和国际大气候的变化相联系在一起的。
“改革开放”已经进行了30年。今天,中国走到了又一个重要转折关头。是走向一个少数寡头利益集团控制的中国,还是走向一个自由、民主、均富的中国,这是今天我们面临的问题。
在《中国不高兴》一书里,王小东和黄纪苏讲内忧外患,但是,我觉得中国主要的不是外患,而是内忧。中国的问题在内部而不在外部。即使外部的问题,它的根源也在内部。中国今天根本的问题是两极分化、社会崩溃。美国5%的人口掌握60%的财富,而中国则0.4%的人口控制了70%的财富。民族主义无力解释中国的现实。杭州飙车案和巴东邓玉娇案典型地说明权力和金钱对于人的压迫和践踏到了一个什么样程度。有权有钱的人拿钱去打一个女孩子的脸。这个动作富有象征意义。有权有钱者认为人们理所当然应为他们提供“特殊服务”。强奸的嫌疑犯一个也没有抓起来,但是,面对强暴奋起反抗的女孩子却被送进了有精神病院,并且以“故意杀人”的罪名将她逮捕了。权力的贪婪暴戾到了骇人听闻、空前绝后的程度。今天在权钱的眼中,所有中国的男人都是太监,所有中国的妇女都是妓女,所有不屈服于权钱淫威的中国人都是精神病人。中国今天的问题在于,权钱勾结,权力资本化,不受约束的权力的贪婪、暴戾和无耻。因此,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制约权力,缩小贫富差距。正如20世纪,民族主义救不了中国一样,21世纪,民族主义同样救不了中国。如果中国简单地以民族主义作为一种替代的意识形态,那么就无力化解国内的阶级矛盾和国外的民族冲突。我注意到何新最近从国家主义向社会主义的转向。在我的心中,他是一个有罪的知识分子。他终于反省: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但是,我要强调,只有民主才能救社会主义。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在宪政的柜架下,扩展自由、民主和人权,创造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生活。






东西模式混淆不清 囫囵一谈 自说自话即便得出正确结论 但对发展脉络的阐述委实荒谬
民族主义的大旗似乎在今日社会各方面需求面前起不了引导作用,反而为资本阶级成为操纵权利的极好的契机。
不知道作者在说什么,结论是什么,资本主义还是社会主义?
作者说“民族主义无力解释中国的现实”,这是正确的。笔者还认为:市场化和私有化也解释不了中国的现实。最能解释中国现实的是什么呢?是专制政体。所以,正如作者所言:“中国目前最重要的是,制约权力,缩小贫富差距”,“事实证明,没有民主,就没有社会主义。中国必须走宪政社会主义道路。在宪政的柜架下,扩展自由、民主和人权,创造自由、平等和有尊严的生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