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引子
1968年5月,一场以学生和工人为主体的社会运动如长虹,如疾风,如暴雷,如骤雨,迅捷地传遍了法兰西大地。这场史称“五月风暴”的社会运动的爆发力度之烈,涉及范围之广,参与人数之多,在法国乃至整个欧美现代史上都是史无前例的。对于这场风暴,言人人殊,总体而言,这是一场以大批抗争学生为前导,以近千万罢工工人为主力,以学生运动和工人运动相呼应为其鲜明特点,同时社会各阶层以不同方式积极参与的反资本主义、反帝国主义和反戴高乐主义的大规模社会运动。
但对当时的不少人来说,这场在短时间内瘫痪了整个法国,并在世界形成深广之连锁反应的社会运动,是突如其来、始料未及的,其中就包括了其时统治法国已近十年的戴高乐总统。就在1967年底,戴高乐向法国国民发表年度广播讲话的时候,还在说:“我以平静的心情迎接1968年……今天的法国绝不可能像在过去那样被危机所瘫痪。”1戴高乐的这个判断被其后政治局势的发展击得粉碎。仅数月之后,巴黎乃至全法国的学校、工厂和街道就被千千万万高举红旗、呼唤变革和革命的人们所占据。开始,戴高乐总统和他的幕僚们试图把这些人描绘为“社会渣滓”,但随着成百上千万的社会各阶层人士深度卷入,这一旨在抹黑的描绘丧失了其意义。
 五月风暴期间的索邦大学,右边悬挂的旗帜上写着“为人民服务”
五月风暴期间的索邦大学,右边悬挂的旗帜上写着“为人民服务”
应当说,参与五月风暴的政治力量是比较多元的,包括无政府主义者、托洛茨基主义者、情境主义者及受其影响的激愤派、社会民主派人士等,当然还包括在其时的法国政坛和社会上举足轻重,尽管在风暴期间组织过罢工,却无意推翻资本主义体制的法国共产党(PCF)及受其控制的法国总工会(CGT),当然我们也不要忘记大批反对风暴的戴高乐主义者。而作为一种独立政治力量的法国毛主义运动,也正是在五月风暴及其后的年代里,才有组织地出现在法国公众的政治视野之中,并对60年代以来的法国产生重大影响。据初步统计,60年代之后,陆续活跃在法国的毛主义团体至少有50多个2,其中影响比较大的有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UJCML,1966-1968)、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1967-1985)、“无产阶级左派”(GP,1968-1973)、“革命万岁派”(VLR,1969-1971)、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UCF-ML,1969-1985)等。
法国毛主义的起源
法国毛主义不是在五月风暴期间从天而降的,它在二战后的法国和世界风云变幻的政治气候中渐次生长出来,是战后法国民众尤其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激进化的产物。促使战后法国青年激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就是1954到1962年间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的独立战争。战争导致法军伤亡十几万人,而阿尔及利亚民族解放军伤亡20万人以上,平民伤亡则在60万人以上。在这场阿尔及利亚的民族解放运动中,号称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政党的法共却支持议会授权法军对民族解放运动进行镇压。1965年秋,法共甚至支持肯定阿尔及利亚殖民战争的政客弗朗索瓦·密特朗参加总统竞选。而另一些所谓的社会主义者——例如莫莱特领导的工人国际法国支部(SFIO),也公开支持法国的殖民战争。除了阿尔及利亚战争外,另一个促使法国青年激进化的因素就是越南战争。在越战问题上,法共以反对冒险主义,避免热核战争为由,打出的只是“实现越南和平”的含糊口号,与此针锋相对,更激进的左翼力量打出的口号是“争取越南人民的彻底胜利”。面对国内如此不堪的修正主义和“左翼”政党,法国的进步青年们只能选择倒向毛主义,托洛茨基主义,或者无政府主义。而在许多反对法共的法国左翼人士看来,“正是毛主义提供了某种过渡形式和依据,使他们得以将斗争重心从殖民地农民斗争转移为国内的工人斗争,他们进而和都灵汽车厂的罢工工人一样承认,‘越南就在我们的工厂里’。”3
进入1960年代之后,毛主义在法国知识界有了长足的影响,这些影响首先是通过法国马克思主义哲学家阿尔都塞的支持产生的。1956年,赫鲁晓夫“非斯大林化”的秘密报告震动了整个世界,尤其对欧美的共产主义运动造成了极其沉重的打击,使得各国共产党员大批退党。欧洲由此出现了“人道主义的马克思主义”潮流,法共也开始主张与其他非马克思主义思想如天主教思想、社会民主主义等对话。在这种情况下,阿尔都塞站出来反对这种把马克思主义解释为人道主义的错误思潮,认为这是对马克思主义的误解,是一种毫不科学的非历史非阶级的分析方法。与此针锋相对,他把自己的学说视为一种“理论上的反人道主义”。在中苏论战期间,阿尔都塞实际上是同情中国对苏联修正主义的批判的,他甚至把其1965年秋出版的著作《保卫马克思》(收录其1961-65年间的文章)寄赠给了中共中央。在他的影响下,作为法国思想家摇篮的巴黎高师中的很多人都变成了毛主义者或亲毛主义者,包括他的学生阿兰·巴迪欧、雅克·朗西埃,以及号称“巴黎高师的列宁”、曾在1967年应邀访华的罗贝尔·黎纳(Robert Linhart)等人。阿尔都塞也同情中国“文革”,作为法共党员,他在毛主义倾向的杂志《马列主义手册》1966年12月号上以化名撰写了一篇分析“文革”的文章,认为“文革”是对以往共产主义运动所出现问题的一种因应之道。
1964年中法建交,法国成为首个与中国建立大使级外交关系的西方国家,中国的思想文化产品得以较顺利地进入法国(如《毛主席语录》《毛泽东选集》《北京周报》等)。这也促进了毛主义在法国的传播。从当时的新锐导演戈达尔1967年的电影《中国姑娘》中,可以很直观地看到这些舶来的中国元素,如红宝书、《北京周报》、北京广播电台的广播等。1967年的巴黎到处充斥着毛主义流行的符号,如所谓的毛氏领套装。该年被称为“中国年”4。
法国毛主义组织的初创与五月风暴的试炼
1960年代早期,法共党内和由法共控制的青年学生组织——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UEC)中活跃着一批亲中的所谓“毛主义分子”。在中苏论争和分裂的大环境下,亲苏的法共对党内的这种“异端思想”毫不容忍。在这种态势下,法共及其控制的群众组织里的亲中分子纷纷被开除。1966年12月10日,由共产主义学生联合会中被清洗或即将被清洗的毛主义者罗贝尔·黎纳、雅克·布鲁瓦耶勒(Jacques Broyelle)、克里斯蒂安·里斯(Christian Riss)、让-皮埃尔·勒当泰克(Jean-Pierre Le Dantec)、邦尼·莱维(Benny Lévy,化名Pierre Victor)等建立了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本文简称共青盟)5,成员多为巴黎高师和索邦大学的文科学生。戈达尔电影《中国姑娘》描绘的就是受共青盟影响的一些年轻人,准确地反映了中苏意识形态分裂对他们的深刻影响。共青盟的领导人是阿尔都塞钟爱的杰出弟子黎纳。他从阿尔都塞以及西班牙农学家卡巴勒罗(Capallero)那里接触到毛泽东思想;尤其是后者向他介绍的毛泽东的“群众路线”思想,给黎纳以极大的震动和启示。黎纳将毛泽东与列宁的思想做了比较,认为:“在列宁的思想中,知识分子应该带给人民一种建立在外部的科学;而毛泽东的思想则认为应该到人民中去,吸取人民的思想元素而建立一种科学,并最终将它送还给人民。”6黎纳深知“什么是政治行动及其优先性”,而这一点是他的老师阿尔都塞所甚为感佩的。在黎纳的批评下,阿尔都塞放弃了自己那个极其著名的哲学定义,即哲学是所谓“理论实践的理论”。7
黎纳领导下的共青盟将自身定位为“同盟”,而不是合格的革命政党,一个重要原因是共青盟的成员基本上都是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同盟”的成立,是为日后能取代修正主义化的法共,建立真正的革命政党。成立初期,共青盟特别重视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的革命化问题,为此创办了卓有成效的理论教育学校。在1967年1至2月举行的第一次大会上,共青盟通过一份政治决议,提出了以下一些政治原则:必须把阶级斗争引到大学和年轻人中去,对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及其修正主义帮凶发动不妥协的斗争;必须对积极分子进行理论上和政治上的训练,创立一个能服务于先进工人和所有革命者的红色大学;必须反对美国和法国帝国主义,支持和学习越南人民的抗美斗争;必须促进服务于工人阶级的革命知识分子的形成,共青盟将创造新的组织形式以达成这一目标。8
在毛泽东“群众路线”思想的指引下,黎纳及其同志们认为共青盟本身过于知识分子化,应该走“群众路线”,创立在共青盟领导或影响下的群众组织,再在此基础上创建一个真正的无产阶级政党。从1967年2月起,共青盟在一些社区、工厂尤其是高中创立了旨在支援越南人民反美斗争的群众组织“基层越南委员会”(Comités Viêt-Nam de Base),吸纳了成千上万的政治积极分子,他们在“五月风暴”及其余波中发挥着关键作用。9 4月29日,共青盟成功捣毁了极右组织“西方”(Occident)在巴黎主办的支持南越政权的展览。“基层越南委员会”取得的极大成功,扩大了共青盟的群众基础,也引起共青盟的政治对手法共的不安。10然而要成为一个不同于已然变修的法共的真正无产阶级政党,共青盟认为必须把工作重点放到工厂去。1967年夏,在毛泽东“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这一思想启发下,共青盟对法国工人(和贫苦农民)的生存状况掀起了大规模的“调查研究”(enquêtes)工作。
 五月风暴中的毛主义者
五月风暴中的毛主义者
到1967年秋,共青盟的调查研究工作转变为对其后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影响深远的“扎根”(établissement)11运动,就是革命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到最广大的人民群众中去,和人民群众一起生活,一起劳动,尤其是要进入工厂中当工人。作为政治语汇的“扎根”的原始来源,据学者研究,是出自毛泽东的表述“安家落户”。12毛泽东在不同场合都强调过“走马看花”、“下马看花”和“安家落户”这三种工作方式。例如1957年3月12日他在全国宣传工作会议上的讲话中说:“我们的国家机关工作人员、文学家、艺术家、教员和科学研究人员,都应该尽可能地利用各种机会去接近工人农民。有些人可以到工厂农村去看一看,转一转,这叫‘走马看花’,总比不走不看好。另外一些人可以在工厂农村里住几个月,在那里作调查,交朋友,这叫‘下马看花’。还有些人可以长期住下去,比如两年、三年,或者更长一些时间,就在那里生活,叫做‘安家落户’。”13
创立“理论教育学校”和“基层越南委员会”,大兴调查研究之风,和“扎根”运动一起,共同形成了共青盟政治活动的鲜明特色。共青盟把“扎根”运动提到很高的高度,认为这是法国马列主义运动发展和创立共产主义政党的必要步骤,是必由之路。14
作为非生产劳动者的共青盟成员离开象牙塔,进工厂当工人,实际上就是一种融工运动,是一种特殊形式的工学结合运动。为什么要融工?共青盟认为,在当时历史条件下,最为先进的革命思想和理论首先为法国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所掌握,但他们本身不能成为革命的领导力量,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革命。但进步知识分子通过把先进的革命理念带入工厂,可以对工人阶级的革命起到一种类似火星、中介或催化剂的作用。那么,在60年代的法国,什么是共青盟眼中先进的革命理念呢?共青盟认为,这就是群众路线,人民战争的战略战术,不断革命论和革命阶段论结合的思想,“为人民服务”的共产主义意识形态,到群众大学校去的思想,以及自我批评和接受群众批评的工作方式等,简言之,就是来自红色中国的毛泽东思想。共青盟融工运动的政治目标是要在先进工人中间创立马列主义革命斗争的工人领导核心。共青盟认为,没有这种领导核心,就谈不上群众工作的进展。工人领导核心的一个重要工作就是要在先进工人中创建秘密组织,打入法共所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在各工厂的分会,促使这些分会革命化,达到重新让法国总工会恢复以前作为“阶级斗争的总工会”之性质的目的。那些到工厂进行“扎根”工作的共青盟盟员负有以下政治使命:在工人阶级中宣传毛泽东思想;促成建立工人核心小组,从而在生产单位中有效地领导阶级斗争;服务于工人核心小组,并与工人核心一起基于群众路线的原则,确立劳工运动中的马列主义策略;在这些先进工人核心的指导下,以共产主义思想陶冶工人阶级。15
这些时称“无产阶级工会主义者”(proletarian syndicalists)的共青盟盟员,从1967年秋开始进行“扎根”运动。到五月风暴开始,这一运动只有不到一年的时间,加上缺乏经验,这一波“扎根”运动成绩有限。根据阿尔都塞的说法,在五月风暴中,工人们并不需要共青盟盟员这样的大学生支持。16也就是说,当时不少工人从根本上仍旧对知识分子抱着一种不信任的态度。但总体而言,五月风暴期间的工人和学生主体在主观上有相互团结、共同斗争的强烈愿望,在实际行动上工人运动和学生运动也是相互呼应、相互支持的。共青盟的进厂“扎根”运动虽然成绩有限,但对其后的法国毛主义有着显著影响,其中有成功的经验,也有失败的教训。
共青盟一开始基本否定学生所掀起的五月风暴,其领导人黎纳认为这是小资产阶级性质的运动。黎纳及其同志坚持认为只有工人阶级才能领导一场真正的革命,没有工人参与,对抗就是没有意义的。同盟领导层甚至认为五月风暴是持改良主义理念的社会民主派人士的阴谋,起到了疏远青年学生和工人阶级的作用。虽然“就与学生抗议运动联合而言,黎纳仍然是坚定不移的”,但他建议学生的示威游行离开巴黎市内的拉丁区,转向大多数工人阶级居住的郊区,以便使学生和工人团结起来。在这种轻视单纯学生运动的思想的指导下,共青盟在五月风暴初期,只是派人在整个拉丁区分发政治小册子《现在就到工厂去》,鼓动学生到郊区的厂区进行活动,而不是积极投入到学生发动的街头斗争中去。17当在一家肉类加工厂“扎根”的妮科尔·黎纳(Nicole Linhart,罗贝尔·黎纳的妻子)提议参加学生的示威游行和街头斗争时,黎纳情绪激动地将她赶出共青盟的会场(虽然事后向她道歉)。黎纳本人还跑到中国大使馆,告诉使馆人员毛主席犯下了一个严重错误,不应该支持法国的学生运动。18
到1968年5月10-11日,五月风暴中的第一次街垒战出现,黎纳相信这是法国资产阶级设下的一个陷阱,为此到法共总部去找他的老对手——法共总书记罗歇商议对策。在遭到门卫拒绝后,黎纳陷入精神危机,不得不服用镇静剂治疗。19在5月中旬工人罢工占厂的态势出现后,共青盟的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成员才积极投入其中,尤其是参加了弗兰(Flins)的雷诺汽车厂和索肖(Sochaux)的标致汽车厂工人抵抗警察的斗争。在风暴之后,同盟还组织了深入法国农村、力图与农民运动相结合的“长征”运动。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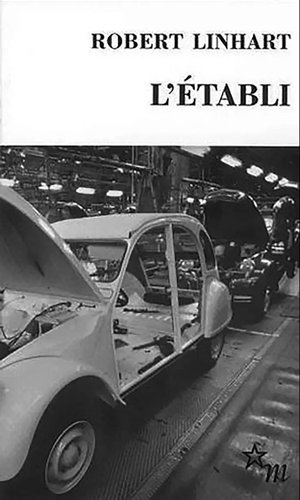 阿尔都塞的杰出弟子、资深毛主义政治活动家罗贝尔·黎纳的名著《工作台 -扎根》
阿尔都塞的杰出弟子、资深毛主义政治活动家罗贝尔·黎纳的名著《工作台 -扎根》
共青盟由于误判形势,基本缺席了五月风暴初期的学生运动。但并非所有的法国毛主义政治力量都在风暴初期交了白卷。与共青盟不同,另一支有组织的毛主义政治力量——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从风暴一开始就支持和参与学生的反抗运动。早在1968年5月5日它就发表声明,开宗明义称“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支持学生反对垄断和法西斯主义权力的正义斗争”,宣称面对法国统治阶级的反动政策,学生们造反有理。声明还宣布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坚定不移地致力于团结年轻知识分子和工人的斗争,它将向工人解释学生斗争的深远意义,并将向学生们提供其战斗性的支持。20在风暴中,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大量印发毛主席语录和小册子,支持学生和工人运动,谴责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的修正主义叛卖,并积极参加历次的街垒斗争。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前史可上溯到1964年。当年,法中友好协会中一些亲中的前法共党员成立了“马列主义界联合会”(Fédération des Cercles Marxistes-Léninstes)。1967年初,联合会改名为法国马列共产主义运动(MCF)。1967年12月31日又改组为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该党长期由雅克·儒尔盖(Jacques Jurquet)领导,得到了中国共产党和阿尔巴尼亚共产党的承认。21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成员相对都比较年长,主要是工人,他们希望几乎全由青年学生和知识分子组成的共青盟接受自己的领导,理由是他们不了解工农,不了解资产阶级,不足以组织群众斗争,但共青盟拒绝了这项提议。共青盟认为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太过封闭,对群众不够开放,认为共青盟自己可以通过走群众路线、向群众学习来解决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提出的问题。总之,两者相互指责对方是精英主义。但共青盟也并不在原则上否定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党建思想,只是否定其在当时这一特别斗争阶段的适用性。总体来说,尽管两个组织在是否在现阶段组建列宁式的纪律严明的先锋党、对方是否为精英主义、是否打入法国总工会以及用何种宣传口号支援越南斗争等方面争议不断,但这两个毛主义组织还是大致保持了一定的友好关系。22
1968年6月12日,也就是在共青盟17岁的高中生盟员托坦(Gilles Tautin)被法国宪兵在弗兰地区溺毙后两天,索肖标致汽车工厂的工人皮埃尔·贝洛(Pierre Beylot)和亨利·布拉谢(Henri Blanchet)为法国防暴警察共和国保安队杀害后一天23,法国内政部长雷蒙·马赛兰发布禁令取缔11个左派组织,其中就包括共青盟和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两个毛派组织。由从法共开除出去的亲华人士克洛德·博利厄(Claude Beaulieu)于1965年成立、坚持刘少奇路线的法国马列主义中心,由于曾在选举中支持过戴高乐政权,也由于在五月风暴中作壁上观,成为没有被戴高乐政府解散的一个法国毛主义组织。24
五月风暴后共青盟的内部论争
被法国官方取缔后,转入地下的共青盟内部爆发了猛烈论争,导致了在1968年夏天的内爆。论争中的一派是以邦尼·莱维为首的少数派,被多数派视为列宁在《怎么办?》中所批判过的、推崇纯粹自发性运动的“自发主义者”(spontanéistes);另一派是多数派,被少数派称为“取消主义者”(liquidateur),这一称呼始于五月风暴前共青盟内部的斗争:当时一些盟员激烈批判共青盟的所谓小资产阶级的唯智主义(intellectualism)、宗派主义和美学主义(aestheticism),同时赞扬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在文化战线等方面的斗争;这种批判实际上表达了这些盟员取消共青盟,力图将共青盟合并进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潜在愿望。在五月风暴后,共青盟内部的这种“取消主义”潜流以新的面目再次浮现。事实上,多数派以总结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为由取消了“扎根”运动,乃至取消了共青盟本身。
 1970 年,戈达尔(前左)、萨特(右三)与波伏瓦(右二)准备到街头散发“无产阶级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
1970 年,戈达尔(前左)、萨特(右三)与波伏瓦(右二)准备到街头散发“无产阶级左派”报纸《人民事业报》
我们知道,列宁在《怎么办?》中认为,“工人本来也不可能有社会民主主义的意识。这种意识只能从外面灌输进去。各国的历史都证明:工人阶级单靠自己本身的力量,只能形成工联主义的意识。”25这就是说,群众的自发性是有限度的,是无法达到革命自觉性的。而共青盟中的少数派则从他们观察到的五月风暴的群众运动经验出发,认为列宁对自发性的批判已过时,因为群众跑到了号称先锋党的各团体的前面去了。他们依据毛泽东的论述“人民,只有人民,才是推动历史前进的动力”,赞扬群众革命的自发性,拒绝基于列宁的先锋队理论而首先建立纪律严明的小团体,认为革命者首先应该走群众路线,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先锋党应该是在群众运动中自然产生的,而不是先建立一个小的自封的先锋党,再去指导群众运动。26他们也建立或帮助建立各种组织,但这种组织不是具体而微的、有严格的纪律约束的先锋党,更多是具体议题导向的组织。这种推崇群众自发性的毛主义,一般称其为自发毛主义(Mao-spontex)。由于spontex也是法国当时一种用以擦拭的海绵的牌子,所以将其称为Mao-spontex,也有戏谑之意。
共青盟多数派的意见是,虽然五月风暴是革命性的群众运动,但因为没有一个纪律严明的强大先锋党领导,所以这一运动不可能成功夺取政权。在五月风暴失败的背景下,他们主张在仓促创建新的先锋党之前,先取消“扎根”运动,回到经典理论的学习,回到书斋和图书馆夯实马列毛主义理论基础,尤其是要有针对性地阅读列宁的《怎么办?》一书。据共青盟少数派领袖邦尼·莱维1971年的说法,五月风暴之后是列宁的《怎么办?》一书在欧洲主要国家被阅读得最多的时期。27而少数派认为,不应该从《怎么办?》这样的书籍来重新出发,要从群众实践,尤其是五月风暴期间所积累的群众实践经验出发,继续投入到自发性的伟大群众运动中去。他们认为,共青盟在五月风暴中犯了错误,这是完全正常的,因为人们没有经验。最好的改正错误的办法是重新与实践连接,通过实践来发现正确的思想。因此需要重新进入工厂,继续“扎根”运动,在工厂和街道的继续斗争中吸取五月风暴的经验教训。28
 1970 年第 24 期《人民事业报》报头
1970 年第 24 期《人民事业报》报头
少数派认为,多数派只看到五月风暴的失败,而对五月风暴在意识形态上的成就几乎一笔勾销,这是其取消主义的一个方面;其另一个方面是取消了共青盟在组织上的成就,不仅是共青盟本身,还包括共青盟在很多工厂已创立的融工组织形式——“扎根”运动。共青盟的绝大部分“扎根”人士(établis)在五月风暴后都放弃了“扎根”活动,离开了工厂。29
多数派(所谓“取消主义者”)和少数派(所谓“自发主义者”)的论争从1968年6月一直持续到1969年2月。论争的结果是转入地下的共青盟的实质解体,多数派的一些人退出现实世界的斗争,转入理论研究,或加入更正统、更重视纪律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少数派在邦尼·莱维领导下,在1968年9月成立新的毛主义组织“无产阶级左派”,另一部分人和南泰尔大学“3月22日运动”的一些人于1969年7月自立门户,成立了典型的自发毛主义组织“革命万岁派”。
法国自发毛主义的兴衰
自发毛主义色彩的“无产阶级左派”成立后,继续践行其母体——共青盟的一些做法,尤其延续了共青盟的“扎根”运动。但共青盟进行“扎根”运动之前着手的大规模“调查研究”,却不太为“无产阶级左派”重视。前共青盟领导人黎纳也加入了“无产阶级左派”。为在工人中扎根串连,没有任何工厂体力劳动经验的黎纳于同年9月去了舒瓦济(Choisy)地区的雪铁龙汽车公司,做了一名普通的非技术工人。日后,黎纳将自己在雪铁龙工厂的经历写成了L’Établi一书。“L’Établi”在法语中有双重意义。一是“扎根”,此处指作者黎纳所属的“扎根”运动,二是指工厂中的工作台。该书以纪实手法,生动细致地描绘了以外国移民为主的雪铁龙汽车工厂工人的工作和生活,也如实记录了作为青年知识分子的作者如何克服种种困难,逐渐赢得工人们的信任,从而成功地组织了一次长达数个星期之久的罢工。30
1969年2-3月,数十名在五月风暴中叱咤风云的“3月22日运动”的活动家加入“无产阶级左派”,大大增强了这一新生毛主义团体的力量,也增强了“无产阶级左派”的自发主义色彩。“无产阶级左派”的影响日渐扩大,成了法国六七十年代影响最大的毛主义团体。“无产阶级左派”的重要活动家除邦尼·莱维和黎纳外,还有阿兰·吉斯玛(Alain Geismar)、雅克·朗西埃(Jacques Rancière)、塞尔日·朱利(Serge July)、克里斯蒂安·让贝(Christian Jambet)、居伊·拉尔多(Guy Lardreau)、朱迪特·米勒(Judith Miller,拉康女儿)等人。“无产阶级左派”致力于反资本主义、反威权主义和反等级主义。从一开始,他们就力图将反威权主义和反等级主义倾向引导到反资本主义的无产阶级革命的道路上,为此于1969年3月出版小册子《从反威权主义革命到无产阶级革命》。“无产阶级左派”的理论家安德烈·格吕克斯曼(André Glucksmann)等更将当时的法国统治者视为新法西斯,将自己人视为“反法西斯游击队员”31;“无产阶级左派”的团队歌曲即称《新游击队员》。
1970年3月,法国政府逮捕了“无产阶级左派”的机关报《人民事业报》的前后两位总编米歇尔·勒布里(Michel Le Bris)和让-皮埃尔·勒当泰克,并宣布如果报贩售卖这份报纸,就会被判一年监禁和永久失去公民权。在政治高压下,曾在五月风暴期间担任全国高等教育联合会领导人的著名运动领袖阿兰·吉斯玛接任《人民事业报》的总编,不久亦被逮捕。“无产阶级左派”此时也被法国政府取缔。但“无产阶级左派”并不气馁,其成员并未溃散,他们继续以“前无产阶级左派”(ex-GP)的名义开展斗争。32在几任总编被逮捕后,毛主义同情者萨特出任《人民事业报》名誉总编,为“无产阶级左派”保驾护航。
1970-71年,“无产阶级左派”在一些工厂,包括巴黎附近比朗古尔的雷诺汽车制造厂、里昂的布朗特和贝利耶厂、南特的巴蒂诺厂、邓科克的造船厂以及北部的煤矿中致力于巩固和建立基层委员会以组织和指导工人斗争。由戈达尔导演、伊夫·蒙当与简·方达等主演的布莱希特式电影《一切安好》(1972),戏剧化地对“无产阶级左派”参与的工人斗争表示了支持。同时,“无产阶级左派”还在中学组建行动委员会,在社会上建立支持越南和巴勒斯坦的组织。另外,一些支援“无产阶级左派”、主要由知识分子组成的外围组织如“红色救援者”、“人民事业之友”、“真理与公平委员会”等也取得了很大的成功。
“无产阶级左派”重视移民工作,在工厂里建立巴勒斯坦支持委员会以吸引阿拉伯工人,同时也支持农民运动,帮助小城镇商人的抗议活动,甚至支持布列塔尼(Brittany)和奥辛塔尼(Occitanie)地区的民族主义分离运动。33总之,哪里有群众的自发性运动,哪里就有他们的身影。为此,该组织受到法国政府的严厉镇压。从1968到1972年,有一千多名“无产阶级左派”人士被关入监狱。这些犯人被法国政府当作普通刑事犯关押,剥夺了其作为政治犯的权利;另外,一些毛主义政治犯在监狱中也遭遇到非人的待遇。所以“无产阶级左派”的一些人跟福柯等一起创建了“监狱信息小组”,发动了影响深远的犯人权利运动。
 1972 年 3 月 4 日,被枪杀的毛主义工人奥维内的葬礼,20 万人在沉默中为他送行
1972 年 3 月 4 日,被枪杀的毛主义工人奥维内的葬礼,20 万人在沉默中为他送行
1972年2月的皮埃尔·奥维内(Pierre Overney)事件是“无产阶级左派”,乃至五月风暴后整个法国革命左派发展的一个转捩点。时年23岁的奥维内是前雷诺汽车公司的毛主义工人、“无产阶级左派”成员。他因参与政治活动而被雷诺公司开除。2月25日,奥维内返回到雷诺公司门口散发“无产阶级左派”的政治宣传品,被该公司的一个保安当场开枪打死,史称“二月枪杀案”。3月4日,绵延长达7公里,由20万人组成的队伍举着旗帜在沉默中为奥维内送葬,其中包括思想界领袖萨特、波伏瓦和福柯。然而法共和法国总工会的人却没有来;对于奥维内的被杀,法国工人也没有起来罢工抗议。奥维内葬礼那天,阿尔都塞不停地对周围的人说:“今天我们埋葬的不是奥维内,而是左派政治。”34奥维内的死亡也象征了五月风暴所引发的工人、学生和知识分子团结的终结。面对毛主义同志被惨杀这一悲剧性事件,“无产阶级左派”的准军事部门“新人民抵抗”决定报复,于3月8日绑架了雷诺公司的一位人事干部。然而这一绑架行动引起了政府和社会的强烈反弹,总统蓬皮杜对此也加以谴责。“无产阶级左派”希望有条件释放被绑架者的企图被政府断然拒绝。“新人民抵抗”的行动也在“无产阶级左派”内部引起了激烈争议。如果为了报复而无限期扣押或伤害这位人事官员,“无产阶级左派”必将招致政府更大力度的镇压;如果将其无条件释放,对奥维内被杀事件不做任何报复,这对于很多毛主义革命者而言,无异于宣告向政权举手投降,也等于宣告“无产阶级左派”一直鼓吹“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号召以暴力反抗“新法西斯主义”政权之宣传的彻底破产。两天后,“无产阶级左派”不得不无条件释放了雷诺公司这位干部。35可以说,奥维内事件是“无产阶级左派”乃至因五月风暴而兴起的整个法国革命左派运动的最后终结。
1973年发生的两个事件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层找到了解散本组织的借口:1973年黎浦(Lip)的贝尚松(Besançon)手表厂工人在夺取工厂后实现了工厂自治,这是法国工人阶级斗争的一次巨大胜利。然而令“无产阶级左派”尴尬的是,这一胜利却不是由当时执革命之牛耳的“无产阶级左派”主导的。同时,在拉丁美洲的智利,社会主义者阿连德领导的民选政府被美国中央情报局支持的右翼力量推翻,阿连德总统本人被杀。贝尚松手表厂工人的成功夺权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导层相信,工人斗争已经成熟,能够实行自治的法国工人已不再需要“无产阶级左派”去领导了。而智利政变使得他们相信,受到中产阶级强力支持的反动力量过于强大,无产阶级革命短时期内看不到成功的希望。这两件事情从正反两方面,使得“无产阶级左派”的领袖们确信,他们的历史使命已经完成,是该结束的时候了。36于是邦尼·莱维等资深干部在1973年底宣布解散组织,同时停止出版《人民事业报》。在1974年1月份出版的“无产阶级左派”系统的杂志《无产阶级手册》中,其领导层对此解释说,组织必须服从于群众运动,任何的组织理论都要依赖于人民革命的理论。而当组织与群众运动的要求不相协调的时候,组织就必须终止。37这实在是一种极为勉强的辩解。组织难道不可以作出调整乃至重组,以适应新的政治形势吗?在革命高潮的时候狂热地投入,在革命低潮的时候灰心丧气,甚至解散革命团体,这其实是一种机会主义的政治态度,是参加革命的小资产阶级两面性的表现。可叹以邦尼·莱维为首的“无产阶级左派”领导层以反对共青盟内部的“取消主义”多数派安身立命,却以另一种版本的“取消主义”解散了自己的组织。随着“无产阶级左派”的正式解散,法国漫长的60年代(1960-1973)才算真正结束。在“无产阶级左派”正式宣布解散后,其内部一些较为年轻的成员拒绝接受这个决定,他们一直将《人民事业报》接编到1976年。
“无产阶级左派”解散后,阿兰·吉斯玛与一些朋友发起了一个公社,转向了“日常生活的革命”;雅克·朗西埃与一些前“无产阶级左派”的同志创办了《逻辑造反》杂志,并开始研究工人档案,编辑出版了《工人的话语:1830-1851》。在“无产阶级左派”中的政治活动经历,给朗西埃的思想烙下了不可磨灭的毛主义的印痕,例如,他在2008年的著作《被解放的观众》一书中写道:“假定有知识的人实际上是无知的:因为他们对于剥削和反抗一无所知,他们本应该变成所谓无知的工人的学生。”38在这里,毛主义的影响卓然可见;塞尔日·朱利等人则联合萨特创立了《解放》报,这份报纸逐渐发展为一份具有中左倾向的法国大报;而1970年代中期以后,“无产阶级左派”运动中的一些前弄潮儿如格吕克斯曼等人则华丽转身,蜕变成所谓的“新哲学家”,他们从修正马列主义转变到猛攻马克思主义本身,完成了从“极左”到极右的变脸过程。
除了“无产阶级左派”之外,另一个影响较大的自发毛主义团体是“革命万岁派”。和“无产阶级左派”一样,它也是由共青盟的一部分人与南泰尔大学“3月22日运动”运动的一些人于1969年7月联合成立的,成立时只有40人,盛期也只是一个几百人的小组织,而且在1971年7月就解体了。“革命万岁派”人数虽少,但它却有着很大的文化影响。
“革命万岁派”的主要领导人有罗兰·卡斯特罗(Roland Castro)和蒂耶诺·格吕巴克(Tiennot Grumbach),其机关报是每两周一期的《一切!》(TOUT!),共发行16期,在法国是第一份广泛发行的分析性、妇女解放、同性恋等问题的报纸。“我们要什么?一切!”他们的这句口号解释了其机关报为什么叫《一切!》。在当时男权思想仍然相当严重的法国左派运动中,革命万岁派是独树一帜的。他们对资产阶级社会的批判,受到带有毛主义色彩的哲学家列斐伏尔日常生活批判理论和维尔海姆·赖希的精神分析学说的强烈影响。与其他毛主义组织一样,“革命万岁派”也派成员到巴黎地区大约20个工厂进行活动,尤其是巴黎第十五区的雪铁龙汽车制造厂。可是当“革命万岁派”成员带着重视“力比多经济学”的《一切!》到工厂时,经常遭到工人的抵制。反感《一切!》这份报纸的人中一部分是在性别问题方面持传统保守态度的人,而另一些人则认为报纸的性政治内容转移了当时工人斗争的大方向。当时的一些左派书店也拒绝售卖他们的出版物。而第12期《一切!》的粗俗化,也使法国政府找到了取缔的理由。39
由于法国政府的镇压,也由于“革命万岁派”内部对相关问题的分歧,使得“革命万岁派”归于解体。但是它的政治和文化活动经验对后来的法国新社会运动,包括法国妇女解放运动(UFL)和同性恋(FHAR)运动,都有着极大影响,这些运动最初也多是由前“革命万岁派”的政治活动分子领导的。40
随着“革命万岁派”和“无产阶级左派”两个团体的解体,自发毛主义大体上在法国落下了帷幕。
巴迪欧的法国毛主义运动批判
早在1960年左右,巴迪欧就积极涉足政治活动,是1960年成立的统一社会党(PSU)的创建元老之一。在巴黎高师期间,他师从阿尔都塞,从阿尔都塞那里接受了强烈的毛泽东思想的影响。巴迪欧等人创立的统一社会党在五月风暴中表现突出,在学运一开始就站到了学生一边。但统一社会党的社会民主主义立场也遭到了共产主义人士的强烈批评。对于巴迪欧来说,五月运动未完成的原因之一正是缺少真正的革命领导层。经五月风暴一役,巴迪欧的政治立场进一步激进化。1969年,他脱离统一社会党,与从“无产阶级左派”脱离出来的娜塔莎·米歇尔(Natacha Michel)、席尔万·拉撒路(Sylvain Lazarus)等人另立毛主义组织——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UCF-ML,或缩写为UCFML)。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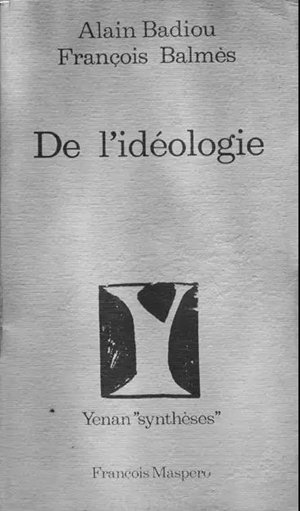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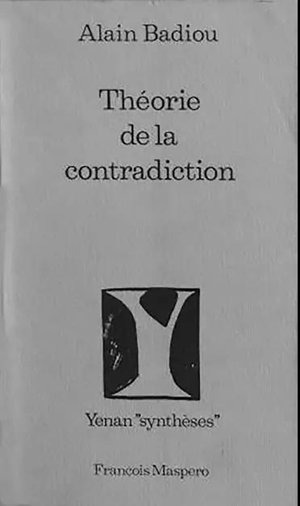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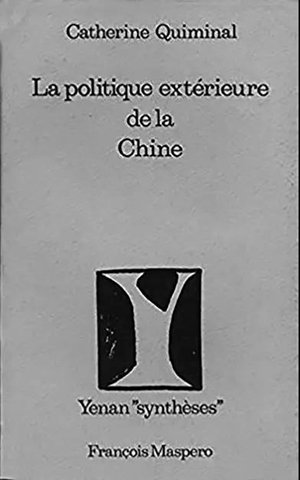 1970 年代中期法国出版的“延安文丛”之“延安综合”系列中的三本著作,左起:巴迪欧的《论意识形态》(与巴尔梅斯合著)、《矛盾理论》 、卡特琳·奎米奈儿的《中国的外交政策》
1970 年代中期法国出版的“延安文丛”之“延安综合”系列中的三本著作,左起:巴迪欧的《论意识形态》(与巴尔梅斯合著)、《矛盾理论》 、卡特琳·奎米奈儿的《中国的外交政策》
为什么要另建毛主义组织?巴迪欧后来声明,是出于对当时毛主义运动日益转向“日常生活政治学”的不满。他也强烈反对“无产阶级左派”做作的、表演性的革命姿态,认为他们常在政治活动中使用欺蒙手法。在后来的访谈中,巴迪欧对此冷嘲热讽道:“几乎所有的无产阶级左派宣传制造的一切有一半是不真实的——本是一只猫,他们却描绘成一只孟加拉虎。”41
巴迪欧对当时法国的毛主义组织做了梳理,认为当时主要有三种毛主义团体:第一种是以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为代表的斯大林主义派,他们反对法共和苏联的修正主义,怀念多列士(Thorez)时代的法共,认为毛泽东领导下的中国正确地坚持了斯大林主义。巴迪欧认为这是对毛主义的一种教条主义的误解,认为他们是“右倾分子”,是保守主义者。第二种以“无产阶级左派”为代表,他们几乎是无政府主义性质的,经常发动一些鲁莽的攻击,也善于表演,说是到群众中去,可是眼睛却盯在媒体上。他们是“左倾分子”。第三种是巴迪欧自己这一派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他称其为“中左”,是处在“左倾”的“无产阶级左派”与“右倾”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之间的毛主义团体。42
巴迪欧等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详尽地调查了法国农民尤其是中西部农民的生活状况,同时在巴黎郊区的棚户区展开工作,也在工厂车间积极组织基层委员会(comités de base),希望为下一轮的法国革命浪潮做耐心和细致的准备工作。43
70年代,巴迪欧写作了大量体现毛主义思想的著作和文章,例如1975年的《矛盾理论》、1978年的《黑格尔辩证法的合理核心》等。1980年代的“冬之年”及其后,巴迪欧对背叛五月精神的前毛主义“同志”如格吕克斯曼等人展开了毫不留情的批判。巴迪欧对这些叛变革命的“新哲学家”的猛烈批判,一直持续到今天。在2008年出版的《萨科齐的意义》一书的英文版序言中,巴迪欧揭下了这些“新哲学家”的画皮:
丝毫不会让人感到吃惊,在1968年的五月风暴及随后的动荡中,一帮骗子聚集在“新哲学”的奇特招牌之下走上了前台,再一次指责革命者,表现出他们对革命的憎恶,歌颂资本主义、议会“民主制”、美国军队以及整个西方。这恰恰是我们的历史中某种冥顽不化的劣根性的延续:可以肯定,这是大众歇斯底里症的令人侧目的爆发,也是臭名昭著的反革命成见的表现。44
余论
始于60年代初期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在1968年五月风暴期间经受了试炼。戴高乐政府1968年6月取缔参与五月风暴的两大毛主义组织——共青盟以及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并没有达到在法国禁绝毛主义的目的。相反,法国毛主义在60年代末和70年代初继续蓬勃发展,出现了有重要影响的两大毛主义团体“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万岁派”。而1972年2月发生的奥维内被枪杀事件是法国毛主义运动的一个转折点,以此为标志,法国毛主义中断了发展的势头。1973年底“无产阶级左派”正式解体,标志着法国长60年代(1960-1973)的终结。虽然在1974年以后,创始于1969年,由阿兰·巴迪欧等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仍继续存在,同时又出现了不少新的毛主义团体,但毛主义运动在法国再也没有此前那种深广的社会影响,在政治上完全边缘化。到1985年,巴迪欧等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亦宣告解体,至此,五月风暴一代的毛主义运动的主体陆续谢幕。但60年代播下的毛主义的星星火种仍被一直传承到21世纪的今天。在今天的法国工厂、学校、社区和网络,仍然活跃着几支有组织的毛主义力量,分别是成立于1979年的“马列主义共产组织——无产阶级之路”(OCML-VP),2002年左右成立的“马列毛共产党”(PCMLM),以及2015年由两个毛主义团体合并而成的“毛主义共产党”(PCM)等。
法国毛主义运动发展到今天,已长达半个多世纪,期间也形成了一些鲜明的特点,值得细致讨论。
首先,法国历史上的一些毛主义团体,以“无产阶级左派”和“革命万岁派”为代表,有着比较强烈的自发主义色彩。如何正确处理群众的自发性与无产阶级政治自觉性的关系,如何处理自发主义的群众运动和先锋党的关系,是关系到一个革命运动能否发展壮大的关键。五月风暴期间的法共“在群众的自发性面前表现出保守的本能,造成了民众运动以明白无误的失败而告终”45。它在风暴期间的彻底沉沦,是国际共运的一个沉重教训。面对一味倡导经济主义和议会道路,反对革命性政治运动的法共的保守和堕落,后五月风暴的法国毛主义者深知创立新的革命政党的重要性。然而,革命者是先根据先进理论创立先锋党以领导自发性的运动,还是先加入到群众实际的、自发性的阶级斗争中去,然后在群众的斗争中形成革命党?在这个问题上,不同派别的毛主义有不同的思路。持后一种思路的毛主义团体就往往具有自发主义的特点。重视并积极投入自发性的阶级斗争和群众运动,就可能在此基础上建立一个更具民主性、人民性的革命政党,也更有可能在群众的自发性运动中抓住转瞬即逝的革命“时机”;然而,对于不少人来说,这种对群众运动纯粹自发性的推崇,忽视对群众运动的领导的做法,不过是一种小资产阶级无政府主义性质的政治偏移而已。
其次是其行动主义(activism)。法国毛主义者在“造反有理”、“哪里有压迫,哪里就有反抗”、“敢于斗争,敢于胜利”等口号的激励下,勇于参加往往具有暴力色彩的斗争,使得法国资产阶级国家机器疲于应对,也取得了不少实际斗争成果。但片面强调斗争性,过于强调直接行动,也使得一些毛主义团体具有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色彩。不能料事在先,不讲究策略就贸然行动,遇到反弹后又没有后手应对,这是其盲动主义和冒险主义的具体表现。例如在奥维内被枪杀事件出现后,“无产阶级左派”的准军事人员抓的不是杀人者,而是雷诺公司的人事官员,使得社会舆论朝向不利于“无产阶级左派”的态势急剧发展,使其不得不很快无条件释放被绑架的人事官员。在盲动主义造成进退两难的不利后果、无法施加有效的反击之后,一些人往往又会一变而为取消主义者和逃跑主义者。
再次,法国六七十年代的毛主义运动具有鲜明的“工人主义”(workerism)色彩。他们认定,工人阶级是革命的天然主体,是革命的天然领导阶级,所以一些毛主义团体把工作重点主要放在工人运动方面。对其他方面的工作,例如学生运动、妇女解放运动等,往往抱着忽视乃至轻视的态度。例如由黎纳领导的共青盟,对学生抗议运动所引爆的五月风暴一开始持不信任甚至轻蔑的态度;所以在五月风暴进行了一周后,共青盟还在忙于派遣革命学生和知识分子到巴黎和外省的工厂去进行工学联合的宣传,或者进工厂“扎根”。这种“工人主义”思想在共青盟的一些年青人那里,甚至达到了一种准宗教的地步。他们带着对工人的无限理想化的美好想象进入工厂,试图在短期内发动工人,在工厂中建立起革命工人领导核心,结果连连碰壁,铩羽而归。根据黎纳在其仍未引起研究者足够重视的杰作《列宁·农民·泰勒》46一书中的观察,这些人往往由对群众的“神秘崇拜”转变为对群众的“厌憎”,甚至在一定条件下(例如处于革命低潮的70年代中后期之后),转变为一种“全然反工人意识形态”的鼓吹者。47对于造成工人、学生和青年知识分子之间关系的疏离,这种人所起的作用也不容小视。五月风暴在不仅革命被“提上了日程”,而且事实上已经是革命的局面下功败垂成,当然跟法共的百般阻挠和叛卖有关,但也跟很多止步于经济斗争的工人对学生运动的观望、怀疑甚至冷漠有关。1968年6月10日毛主义学生托坦为宪兵溺毙,对这件震动全法国的事件,法国工人没有起来罢工抗议,就很说明问题了。当然,“秩序党”法共及其控制的法国总工会应该对一部分工人的这种政治冷漠负主要责任,因为作为控制了法国工人中的很大一部分的政治力量,它们平常用来教育工人的,基本上是去革命化的议会主义、和平道路和一些去政治化的经济主义算计。但如上所述,某些毛主义知识分子形而上学性的“工人主义”思想及其对工人运动机会主义、功利主义的利用,也对工人的政治冷漠起到了推波助澜作用。阿兰·巴迪欧就在1969年对共青盟的“工人主义”做过剖析,认为共青盟的一些激进分子是“工人主义”这种“革命运动中的严重弊病”的牺牲者。巴迪欧认为“工人主义”由三种互相联系的错误构成:对工人生活的感情用事的描绘;对工人自发性的盲目信仰;以及认为革命可以由工人阶级单独进行,而不是由工人、学生和贫苦农民所构成的人民联合阵线来进行。48巴迪欧对“工人主义”的批判足以警醒后人。
要言之,半个世纪以来法国毛主义运动的问题,还是毛泽东早已指出过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的问题,是一个倾向掩盖另一个倾向,一点论压倒两点论,形而上学遮蔽辩证法的问题。如何克服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是未来的任何毛主义运动都要解决的重大问题。推动此类问题的解决之道,可能还是要先回到毛泽东所倡导的工作思想和工作方法,也就是从事实际的革命行动之前,要大兴调查研究之风。1967年夏,法国的共青盟在调查研究方面做过一些尝试,可惜由于历史给予该团体的时间太短,这一尝试开始不久就夭折了。而70年代以后残存或新兴的法国毛主义力量,除了巴迪欧领导的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同盟之外,似乎久已没有大兴调查研究之风了。21世纪的法国还会有新一轮毛主义运动的兴盛吗?在信息资本主义时代,它还会有生命力吗?有志于毛主义在法国之复苏的人们,可能除了要对现实进行详尽深入的调查研究外,还要对过去半个多世纪的法国毛主义运动历史进行全面盘点,对其起源、发展、兴盛、衰落以及承续至今的脉络进行精细的梳理。历史上,法国毛主义有其顺势而为,快速发展的经验,亦有其左冲右突,进退维谷的困境;其经验和困境,都充分体现在众多法国毛主义团体的丰富理论和实践中。也许可以说,忽视对社会现实的调查研究,不对历史上毛主义的经验教训做出很好的理论总结,扬其长而避其短,就解决不了毛主义运动实践中存在的经验主义和教条主义问题,也就谈不上毛主义运动的未来。在对法国毛主义的研究方面,尽管国外已经有了不少初步的成果,但总体上说,这一议题并没有得到充分展开。限于学力,本文处理法国毛主义的理论和实践,可谓浅尝辄止,难免挂一漏万,豕亥相淆,希望能引发有识之士对这一课题的更精彩讨论。
注释:
1 Johan Kugelberg and Philippe Vermès (eds.), Beauty is in the Street: A Visual Record of the May
’ 68 Paris Uprising, Four Corners Books, 2011, p.76.
2 据法文网站archivesautonomies.org的统计。
3 [美]克里斯汀·罗斯:《1968年5月及其死后之生:导言》,赵文译,载《生产》第6辑《五月风暴四十年反思》,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24页。
4 [美]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董树宝译,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第116页。
5 其中黎纳、布鲁瓦耶勒、里斯和勒当泰克,与另一位学生斯图尔姆(Sturm)等五人在1967年8月应邀访华一个月,坚定了他们对毛主义的信心。关于他们访华的情况,参阅[法]弗朗索瓦·杜费、皮埃尔-贝特朗·杜福尔:《巴黎高师史》,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8年,第136-137页。
6 同上书,第129页。
7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蔡鸿滨译,陈越校,上海人民出版社,2012年,第231页。
8 见《马列主义共产青年同盟第一届第一次会议政治决议》,出自1967年1、2月合刊的《马列主义手册》(Cahiers Marxistes-Léniniste) ,总第15期。
9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63页。
10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A Memoir, translated by Richard Veasey, New Press, 1994, p.354.
11 établissement这个词亦可译为“据点(组建)”。
12 “安家落户”英文一般翻译成“settling down”,法文翻译成“s’établir”。See Donald Reid’s “Etablissement: Working in the Factory to Make Revolution in France”, Radical History Review 88 (Winter 2004): p.86.
13 《毛泽东文集》第七卷,人民出版社,1993年,第272页。
14 参见共青盟1968年的文件《论扎根》( Sur l’éta-blissement),英译文见网刊《视点杂志》(viewpointmag.com),2013年9月25日上线。
15 参见共青盟1968年的文件《论扎根》。
16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第354页。
17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94页。
18 Donald Reid, “Etablissement: Working in the Factory to Make Revolution in France”,p.88.
19 Ibid.pp.88-89.
20 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PCMLF)1968年5月5日《新闻稿》,原文见法国“共产主义档案”网站(archi-vescommunistes.chez-alice.fr)之PCMLF历史档案部分。
21 关于法国马列主义共产党的政见及其演进和分裂情况,参见[法]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年,第126-128页;Robert J. Alexander, Maoismin the Developed World, Praeger Publishers, 2001, pp.68-72.
22 See Belden Fields, “French Maoism”, Social Text, No.9/10,1984, p153;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 Maoism: Theory &Practice in France & the United States, Autonomedia,1988, pp.91-92.
23 “没有人死于1968年事件”是一句谎言,除了这里列出的三位死难者之外,还有更多的人死于五月事件。关于主流叙事炮制所谓“没有人死于1968年事件”谎言的政治逻辑,可参阅杰出的五月风暴研究学者克里斯汀·罗斯在其名著《1968年5月及其死后之生》(May’68 and Its Afterlives)导言中所做的分析。
24 Belden Fields, Trotskyism & Maoism: Theory & Practice in France & theUnited States, p.72.
25 列宁:《怎么办?》,人民出版社,1971年,第30页。
26 Benny Lév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oists in France(1971)”,文章收录于国际托派网站“马克思主义网络文库”(marxists.org)。
27 Ibid.
28 Benny Lévy, “Investigation into the Maoists in France(1971)”.
29 Ibid.
30 黎纳此书有英译本,See Robert Linhart, The Assembly Line,University of Massachusetts Press, 1981.
31 格吕克斯曼关于法国“新法西斯主义”的论述,参见[法]戈夫:《1968年5月,无奈的遗产》,第164-166页。
32 “前无产阶级左派”(ex-GP)是“无产阶级左派”被当局取缔后使用的名字。后文为叙述方便,仍将1970年被禁后出现的所谓“前无产阶级左派”表述为“无产阶级左派”,因为两者实质上是一回事。
33 Belden Fields,“French Maoism”, p.153.
34 Louis Althusser, The Future Lasts Forever: A Memoir, translated by Richard Veasey,p.232.
35 关于奥维内事件,可参阅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12-13页。
36 Belden Fields, “French Maoism”, p.172.
37 Cahiers prolétariens , n°2, janvier 1974.
38 Jacques Rancière, The Emancipation Spectator , Verso, 2009, p.18.
39 Belden Fields, “French Maoism”, pp.154-155.
40 对于“革命万岁派”的翔实研究,请参阅 Manus McGrogan, Tout! in context, 1968-1973: French radical press at the crossroads of far left, new movements and counterculture, PhD thesis (University of Portsmouth, 2010).
41 Badiou,“On Different Streams Within French Maoism”, 文章收录于美国毛派网站kasamaarchive.org(该网站已停止更新)。
42 同上。
43 理查德·沃林:《东风:法国知识分子与20世纪60年代的遗产》,第173页。
44 巴迪欧:《〈萨科齐的意义〉英文版导言》,鞠振、王志超译,《国外理论动态》,2010年第6期。
45 阿尔都塞:《来日方长:阿尔都塞自传》,第247页。
46 Robert Linhart, Lénine, Taylor, les paysans , Paris:Seuil, 1976.
47 JasonE. Smith, “Fromto Lip: On the Turns Taken by French Maoism”,见网刊《视点杂志》(viewpointmag.com)第3期“工人探索”(Workers¡¯ Inquiry)专号。
48 Jason E. Smith, “Fromto Lip: On the Turns Taken by French Maoism”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能够更好地服务于关注网站的老师和朋友,激流网现推出会员制度:详见激流网会员办理方案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蒋洪生。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李大壮)
(作者:蒋洪生。来源:文艺理论与批评。责任编辑:李大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