按:近日的欧洲议会选举中,气候和环境议题占据了选战的焦点。选举前的民调显示,气候与环保议题已经超越了社会保障、安全与移民问题,成为了选民最关注的议题,这被认为是传统中左、中右翼政党流失选票而德国绿党一路飙升成为最大赢家的原因。不过生态问题并不向来是左翼进步议程的一部分,从最近发生的新西兰清真寺恐袭案凶手发表的宣言《大替换》,到两年前“另类右翼”一词的缔造者、白人至上主义领军人物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在夏洛维尔“联合右翼”集会期间发布的法西斯主义纲领《成为另类右翼意味着什么》,我们都能从中找寻到生态议题的线索。事实上,生态学在二十世纪就有着一段与法西斯主义纠缠不清的历史,它在法西斯主义“血与土”的逻辑下,成为了反移民的帮凶——普通民众在生态话语的鼓励下,开始相信无根的外来民族(犹太人)会破坏本土的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质。而“生态法西斯主义”也并未随着纳粹的消亡而消亡,它持续回响在后来的很多运动之中。如《生态法西斯》一书的作者指出,如果一场社会运动只有“生态”取向却没有社会批判意识,那么它将是十分不稳定的。而一种解放性的生态政治需要对古典生态法西斯主义及其当代延续性有敏锐的意识。这个意识也一再提醒着活跃于今天世界各地的可持续农业运动——拒绝法西斯主义的渗透!
 20世纪初将环境保护与种族主义紧密相连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德国青年运动“游鸟”(Wandervögel),大部分成员后来被纳粹党吸收。
20世纪初将环境保护与种族主义紧密相连的思想付诸实践的德国青年运动“游鸟”(Wandervögel),大部分成员后来被纳粹党吸收。
2019年3月15日的新西兰克赖斯特彻奇(Christchurch)清真寺枪击事件震惊世界。袭击者准备周密,对这场造成50人死亡的屠杀进行在线直播,在事前还发布了一份长篇“宣言”,号召以武力反抗针对白人的“人口替换”,并在其中自称“生态法西斯主义者”。这个标签令人困惑。当“法西斯”早已成为一个人人避之不及的政治羞辱用词的时候,有人自称“法西斯”究竟是什么意思?众所周知,历史上的法西斯疯狂追求军事化和工业化,能与生态有何干系?
但是了解法西斯历史的人,从中生态修辞中能一眼看出当今白人至上主义者与法西斯主义的深层精神联系,同时牵带出生态学一段充满麻烦的历史。
法西斯主义的归来
事实上,这名来自澳大利亚的恐怖分子是一场全球性的法西斯主义复兴运动的成员。对他们来说,法西斯不是一张丑陋的标签,而是一种可取的思想。这场运动在美国被叫做“另类右翼”,在欧洲则有着与之对应的 “身份主义运动”(Identitarian Movement),克赖斯特彻奇的恐怖分子与之过从甚密。在媒体上,这些新的民粹运动也经常被称作“极右翼”或“白人至上主义者”,但是,二战后主导政治立场划分的线性的“左”和“右”已经不能够准确界定正在快速兴起的民粹政治。克赖斯特彻奇事件中的恐怖分子在“宣言”中声称自己既是“左派”,又是“右派”,但同时又说这取决于左右的定义。
 2019年4月13日,奥地利维也纳,极右翼举着“身份主义运动”标识的旗子集会
2019年4月13日,奥地利维也纳,极右翼举着“身份主义运动”标识的旗子集会
但是,他却明确称自己是“法西斯主义者”。 法西斯主义作为一种意识形态,在20世纪上半叶兴起时的含义包括恢复某一种族或民族的尊严和优先性,反抗外来种族和思想破坏主体种族与其故土的天然联系,宣扬对祖国的崇拜,将社会军事化,歌颂斗争、英雄主义、领袖和男性气质。但是在二战后,它的固有含义渐渐剥落,“法西斯”经常被等同于“极端主义”和“暴政”,成为一个政治谴责和攻击的标签,参与议会选举政治的政党都不愿被打上这个标签,而新纳粹团体则都处于社会边缘。但是在2016年底特朗普当选美国总统后,法西斯主义者开始蠢蠢欲动,想让这场运动重新混上历史的台面。
2017年8月11和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举行的“联合右翼”集会,是对这种冲动的隆重宣示。这起事件更多地以一名白人至上主义者驾驶轿车冲入反对派游行队伍,造成一人死亡20多人受伤,以及事后特朗普以对双方“各打五十大板”的方式向白人至上主义阵营表示默许而被人们记住。但更值得注意的,是这场集会多么明目张胆地宣扬法西斯主义信条。
 2017年8月11和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举行的“联合右翼”集会
2017年8月11和12日在美国弗吉尼亚夏洛茨维尔(Charlottesville)举行的“联合右翼”集会
在8月11日晚的弗吉尼亚大学的“火炬游行”上,数百名白人至上主义者挥舞着火炬列队进行,齐声高呼三句口号“你们不会替换我们”、“犹太人不会替换我们”、“血与土”。前两句,来自当前全球新法西斯主义者普遍信奉的阴谋论学说,认为白人人口将(在犹太人的策划下)被生育率过高的移民“大替换”。“大替换”论起源于法国右翼知识分子、身份主义运动的理论家之一Renaud Camus出版于2012年的同名书,也被新西兰恐怖分子用来命名他的“宣言”。而“血与土”是纳粹党的著名口号,指一个种族与一块领土有着天然的、受自然规律支配的排他性联系。
这些集会者挥舞万字旗、行纳粹礼,有的还身着形似纳粹的制服,面对媒体或在他们自己撰写的“宣言”中,都毫不忌讳地自称法西斯主义者或纳粹。对他们来说,“法西斯”被污名化了,它是一场需要被重振的运动。
那么,法西斯主义者为什么要谈生态?简单地说,因为法西斯主义者强调种族与土地的天然联系,谈生态有助于强化这种联系,为消灭“入侵者”、淘汰不适者找到理由。
新西兰恐怖分子并不是这一轮法西斯运动中唯一谈论生态的。“另类右翼”(alt-right)一词的创造者Richard Spencer在2017年8月11日夏洛茨维尔集会首日发布的宣言《成为另类右翼意味着什么》是一份典型的法西斯主义纲领,强调白人的诸“欧洲民族”的整体性和优先性,敌视犹太人,强调人类社会受生物规律的支配、女性对民族负有生育责任,反对全球化以及“生意人和全球商人”的利益凌驾于工人和自然之上。在其20条纲领中,有一条题为“自然世界”,它写道:“我们是自然秩序中特殊的一部分,既在其中又在其上。我们既有能力成为自然的守护者,也可以成为它的毁灭者。放下像气候变化和资源枯竭这些争议性议题不谈,欧洲国家应当投资于国家公园、荒野保护区、野生动物栖息地,以及生产性和可持续性的农场和牧场。自然世界,以及我们对它的经验,本身就是目的。”——如果不知道写作者的背景和这背后的政治议程,这可以说是一段对人与自然关系的相当中肯的反思,而且它并不否认气候变化,而是试图争取对它持不同看法的人对环境保护达成共识。
而在新西兰恐怖分子的宣言中,有一节是“绿色民族主义是仅有的真正的民族主义”。他在其中责备民族主义阵营长期听任左翼窃取环保议题,把环境破坏的终极原因归咎于不受控制的移民。他甚至不像Spencer那样搁置气候议题,而是承认是人为因素导致了气候变化,只不过这个“人为因素”是人口过多。但他认为白人没有过度生育,过度生育的是那些被他称作“入侵者”的非白人移民,因此为了拯救环境,杀死后者是正当的(哪怕事实上他们的碳足迹和资源消耗远低于富国中的白人)。他同时斥责“保守主义者”(conservatives)“什么都没能保守(conserve)住”,他们丢掉的不止是国族、种族、宗教、文化,还有环境——“自然环境被工业化、碎片化和商品化了”,这名凶手写道。
但是,这两名极端主义者的思想都不具有什么原创性,而只不过是重拾了一场已经存在两百年的、推动了法西斯主义崛起的种族主义、民族主义与生态学之间的联姻。
生态法西斯往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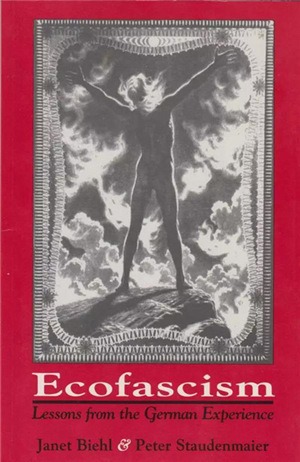 《生态法西斯:来自德国经验的教训》
《生态法西斯:来自德国经验的教训》
由美国历史学者Peter Staudenmaier和作家Janet Biehl合著的《生态法西斯:来自德国经验的教训》(Ecofascism : Lessons from the German Experience)出版于1995年,书中系统梳理了德国生态法西斯主义的起源、它与纳粹运动的结合,及其二战之后的“现代化”过程,从19世纪上半叶一直写到20世纪90年代。
书中将“血与土”这一神秘主义学说的起源追溯到两名19世纪学者——恩斯特·莫里茨·阿恩特(Ernst Moritz Arndt,1769~1860)和他的学生威廉·海因里希·里尔(Wilhelm Heinrich Riehl,1823~1897)。
阿恩特是日耳曼民族主义和德意志统一运动中重要的活动家,曾参与反对拿破仑统治的斗争。早在他1815年的文章《论对森林的照料和保育》(On the Care and Conservation of Forests)中,他就批评工业革命对森林和土壤的破坏,认为自然是一个相互关联的整体,草木、石头、虫子、人类,都只是其中的一部分,不分先后。而他的学生里尔在1853年发表的文章《田野和森林》中甚至提到了“荒野的权利”,令人不禁想起2008年厄瓜多尔左翼科雷亚政府将“自然的权利”(rights of nature)写入宪法。
但是,他们这些具有前瞻性的生态观却总是与排外民族主义乃至种族主义结合在一起。他们要守护的自然,是“德国的”自然,要守护的土地,是“德国的”土地。与此同时,阿恩特反对混种生育、宣扬日耳曼人的种族纯洁,同时鄙夷法国人、斯拉夫人和犹太人。而里尔则在《田野和森林》中写道:“我们必须保护森林,[……]这样德国才会一直是德国的”。
里尔被人称作“乡村浪漫主义和反都市主义的奠基者”。他不仅批判工业化造成的环境破坏,而且把批判矛头直接指向工业化、都市化乃至现代性本身。他的这种思想倾向,后来成为19世纪下半叶德国强有力的“民族性运动”(völkisch movement)的核心要素,这场运动让生态神秘主义和种族主义更加牢固地结合在一起。“民族性运动”号召德国人“回到土地”,寻找某种人与土地源自太古的联系,它将时代的种种问题归罪于理性主义、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和都市文明。而无根漂泊的犹太人,是这场叫做“都市工业文明”的阴谋的幕后主使。
《生态法西斯:来自德国经验的教训》一书认为,生态学(ecology)的命名者和开创者、动物学家欧内斯特·海克尔(Ernst Haeckel,1834~1919)也贡献于纳粹意识形态的形成。他的“一元论”(monism)认为,人类和动物之间没有形而上学的差别,而是受制于同样的规律,因此人类并不凌驾于自然界。他也是达尔文进化论思想在德语世界的重要传播者,但是他认为,进化法则同样适用于人类文明,优势种族有权主宰其他种族,他支持优生学、北欧种族优越论,反对人种混合。(不过也有学者认为,海克尔事实上对犹太人抱有积极看法,而他的思想后来也被纳粹党抛弃)。海克尔及其门徒Willibald Hentschel、Wilhelm Bölsche和Bruno Wille等,被认为强有力地塑造了此后德国的环境思想,这种思想把对自然保护的强烈关切与民族主义紧紧结合在一起。
时间来到20世纪的最初30年,当时兴起的德国青年运动“游鸟”(Wandervögel)将以上思想付诸实践。它的名字来自于其成员经常结队在山野中长途跋涉,宣扬通过“回到自然”来获得个人自由,建立个人责任意识和纪律性。其思想混合了新浪漫主义、东方哲学和自然神秘主义,向往牢固的社群纽带和未被异化的社会关系,它敌视理性主义,认为是工具理性破坏了自然,造成了人的疏离。大部分“游鸟”成员后来被纳粹党吸收,把这些思想带入了纳粹党。
1933年纳粹党上台,其中多名高级领导人具有这种试图重建人与自然联系的倾向。希特勒的确是一个素食主义者。但他不仅素食,而且热爱动物,反对活体解剖,采用顺势疗法,甚至还谈论以水电和沼气替代煤炭,宣称“水力、风力和潮汐力是能源的未来之路。”希特勒在《我的奋斗》中呼应海克尔和一元论者的论调,认为人无法逃脱自然的铁律,他写道:“他们(试图摆脱自然铁律的人)反对自然的行动必然导致他们自己的垮台。”除了希特勒,《生态法西斯》一书指出,纳粹领导层中具有多神信仰(paganism)的成员——包括党卫军首领海因里希·希姆莱(Heinrich Himmler)、第三帝国东部占领区政府局长阿尔弗雷德·罗森堡(Alfred Rosenberg)和食品和农业部长理查德·沃尔特·达里(Richard Walther Darré)——也具有同样的倾向。无论是在第三帝国时期还是在当代,神秘主义信仰与法西斯主义生态观之间的联系不断出现,这使得西方社会中将自然神秘化的生态观常被投以怀疑的眼光。这是后文将会谈到的话题。
《生态法西斯》一书还引用历史学家Klaus Bergmann的研究写道:纳粹党的主要意识形态理论家们都或多或少地都倾向于乡村浪漫主义,敌视都市文化,认同一定程度的“再乡村化”的必要性。这种乡村浪漫主义伴随着对呵护自然环境的注重。希姆莱在1942年关于将波兰被占领土建设成日耳曼人的“生存空间” (Lebensraum)的文章中写道:“我们种族的农民自古以来精心呵护并提升土壤、植物和动物的自然力量,并平衡整个自然界。”他认为,如果要让新占的“生存空间”变成日耳曼人的理想家园,那么尊重自然的规划是必须的,只有生活在这样的环境中,才是最强种的。
而以达里为首的一批技术官僚,则热切地将生态意识形态落实为环境保护实践,他们被称作纳粹中的“绿翼”。
达里在1930年的一场演讲中说出一句“血与土的统一必须恢复”,正是这句话“血与土”变得著名,并在后来成为纳粹官方意识形态。达里还致力于将环保原则注入第三帝国的农业农业政策。他借鉴了奥地利哲学家鲁道夫·斯坦纳(Rudolf Steiner,1861~1925)的“人智学”(anthroposophy)和“生物动力农耕”(bio-dynamic farming)思想,创立了一套名为“生命规律农耕”(lebensgesetzliche Landbauweise)的有机农业方法。
他们还关心风景的民族性。装备和军火部长弗里兹·托特(Fritz Todt)在负责建设德国的高速公路系统时,曾要求这些公路能够“成为对周边风景之表现,和对德国本质的表现。”
纳粹绿翼的最大后台是纳粹三号人物鲁道夫·赫斯(Rudolf Hess)。在他的支持下,纳粹绿翼得以从1933年起推行了一系列中央和地方生态立法,内容从森林复植到动物保护。1935年的《帝国自然保护法》要求各级政府在开展对乡野造成重大影响的工程前必须咨询自然保护局,并限制对尚存荒野的商业开发。这些都被认为跻身当时世界上最进步的环保法规之列。30年代中期,托特及其副手曾试图推行一部包罗万象的《帝国地球母亲保护法》,但最终由于经济部长以担心影响矿业为由反对而未能落地。
与此同步的是环保工作者中遍布政治积极分子。《生态法西斯》一书引用的一项对魏玛时期自然保护组织的调研显示:到1939年,这些组织中已有60%的成员加入了纳粹党,而同时期,成年男性教师和律师加入纳粹党的比例仅为25%。
但是,并非所有的纳粹党高层都热衷生态问题。宣传部长戈培尔、希特勒秘书鲍曼和党卫军副总指挥海德里希就认为绿翼是一群不可靠的梦想家,或者干脆就是安全隐患。而最终,也正是由于绿翼的政治后台鲁道夫·赫斯在1941年独自飞往英国谈和,使这一派系走向瓦解。但是恶果已经结成,生态话语让原本温和的民众也变成狂热的民族主义者,无根的外来民族被视为本土自然环境和民族特质的破坏者,这让大屠杀也具有了合理性。这一逻辑在新西兰清真寺的枪声中得到了恐怖的回响。
但是如今在西方和拉美国家,人们已经习以为常地认为环保是左翼的议题,而“右翼”、“保守派”则通常不惜一切代价捍卫自己污染的权利,把环保描绘为旨在阻碍经济发展、妨碍个人自由、乃至是推行集权统治的“社会主义阴谋”,有时甚至给环保主义者贴上“法西斯分子”的标签。但是,放到更大的历史尺度下来看,情况就不是这么两分。《生态法西斯》一书引用史学家的观点指出,对自然破坏的关切事实上来自各种意识形态背景,“生态学”本身并不必然意味着何种政治立场,而取决于对生态问题成因的解读。左翼——从福利自由主义到社会民主主义、无政府主义再到部分马克思主义者——面对环境问题,通常致力于分析造成破坏的社会关系,把矛头指向不受约束的工业资本(无论是私有还是国有)。而民族主义极右翼则认为自然破坏是因为自然秩序受到干扰,因此要保护环境就要肃清这些干扰因素——外来人口。
美国生态哲学家Michael E. Zimmerman在他的《生态法西斯主义:一种持久的诱惑》一文中还区分了当今美国语境下的 “右翼”和“极右翼”。“极右翼”是前文已经讨论的类型,它藐视个人自由,而“右翼”(也叫“保守主义”)的实质是新古典自由主义(neo-classical liberalism),他们崇尚个人自由、小政府,将环境保护和环境监管视为对个人自由的侵犯。这些崇尚自由市场、资本友好的右翼对自然的无视态度恰恰是历史中的异类。在这个意义上,新西兰恐怖分子在他的“宣言”中指责保守主义者没能“保守”住自然,确实击中软肋。
可见右翼和极右翼之间的光谱并不连续,而是有着构造的不同。但是,两者在反对移民这一点上却经常站在同一条战线上,这是后文会涉及的话题。
《生态法西斯》一书的作者特别指出,二战后德国的环境运动曾否认生态问题的政治性,绿党成员曾骄傲地声称自己“既不左翼也不右翼,而是在前峰”,这造成绿党被法西斯成分渗透(另据报道,美国和加拿大绿党也都曾经驱逐内部的极右翼成分)。作者指出,如果一场社会运动只有“生态”取向却没有社会批判意识,那么它将是十分不稳定的。而一种解放性的生态政治需要对古典生态法西斯主义及其当代延续性有敏锐的意识。书的下部就追踪了生态法西斯在二战后的遗族。
 1993年8月14日,新纳粹组织在德国富尔达发起的“鲁道夫·赫斯游行”,聚集了上百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本土的激进新纳粹。
1993年8月14日,新纳粹组织在德国富尔达发起的“鲁道夫·赫斯游行”,聚集了上百来自法国、比利时和德国本土的激进新纳粹。
比如“国民革命者”(National Revolutionaries)运动声称试图弥合左右分野,走出一条基于民族主义和“具有民族特色的社会主义"(socialism of the specific national way)的道路,相信这是德国对人类负有的使命。不能忘记,纳粹主义的全称正是“national socialism”。
其中一个叫“团结主义者”(Solidaristen)的派系追随20世纪20年代纳粹党早期成员施特拉瑟(Strasser)兄弟的路线,强调“国家社会主义”中的“社会主义”成分,反对资本主义,甚至将后来被驱逐出党并流亡国外的弟弟奥托·施特拉瑟视为“国家社会主义的托洛茨基”。同样挑战人们对意识形态界线的认知的,是它还支持一系列民族解放运动——爱尔兰、巴斯克、乌克兰、阿富汗乃至尼加拉瓜马克思主义政党桑蒂诺民族解放阵线。“国民革命者”认为,二战后的德国是被帝国主义占领,试图解放它,并实现与奥地利的统一。
其主要的意识形态领袖激烈反对基督教,认为它们是“(经济)增长的宗教”,被对生产力的崇尚所绑架。而为了培养出一种国族认同,就需要创造一种结合了日耳曼新多神论(neo-pagen)信仰、凯尔特和印度宗教与“völkisch”民族主义理念,以仪式、舞蹈和禁忌、冥想和狂喜为基础的新宗教。从而重新建立人与自然的联系,克服异化,重新发现自我。
值得注意的是,“国民革命者”运动不只是利用生态修辞构建民族主义,他们也确实参与了环保运动。比如,他们在70年代投身反核能运动;70年代末部分成员加入了新生的绿党,甚至担任了职务,直到在1980年被认为过分危险而遭到驱逐。
又比如成立于1979年、1995年被宪法法院裁定为非法的自由德国工人党(Freiheitliche Deutsche Arbeiterpartei)。它支持“国家社会主义”,赞美德国士兵在两次世界大战中取得的成就,要求将就业机会留给德国人、遣返外国人、不给外国人特许经营权,反对社会融合。他们还试图重建纳粹党并团结各路法西斯主义者。作为希特勒而非施特拉瑟兄弟的信徒,他们不寻求与左翼的和解,而是将马克思主义和自由主义、基督教一起视作“撕裂人类与我们的地球的自然周期的联系”的罪魁祸首。他们反对堕胎、支持动物福利,认为“技术环保主义”不能应对日益恶化的生态灾难,而是需要发动一场“生态革命”和“意识革命”,将人类重新整合到“地球生命结构”中去。
还有创立于1983年的“共和党人”(Die Republikaner),自称为“德国爱国者的社群”,否认与纳粹的联系,但是其政纲却带有“血与土”的印记。他们反对移民、主张德国是“德国人的德国”,要求保护德国种族健康,反对德国妇女堕胎——但是,他们却认为第三世界限制生育是必须的,以防“人口爆炸”危害环境。
《生态法西斯》一书的记录止于上世纪90年代上半叶。到2012年,媒体报道了由前纳粹党员创立于1964年的国家民主党(NPD)开始出版一本有机农业杂志来宣传极右翼思想。报道同时揭示,从上世纪90年代开始,在国家民主党的支持下,持极右翼政见的人口陆续迁往德国东北风景如画但人口凋零的前东德农业地区梅克伦堡(Mecklenburg)定居耕作,试图恢复纳粹时期的“血与土”农业浪漫主义运动“农人联盟”(Artamanen-Gesellschaft)。他们提倡有机农法、呵护土壤、反对工业化的动物养殖、转基因种子和化学杀虫剂,其不仅出于保护环境,也出于反对资本控制农业、为农民和农产品消费者争取权利的主张与左翼环保运动一致。
这些“殊途同归”,让关于生态法西斯的讨论变得更加麻烦。一种环境和农业主张既可以是“绿色”,也可以是“褐色”(纳粹冲锋队制服的颜色),若不加分辨容易误入歧途。
不应有的误解
读到这里,可能已经有人欣喜不已,以为找到了唾弃有机农业的新证据,迫不及待要给它打上一张法西斯的标签,让它永远失去挑战他们崇拜的“农业现代化”的资格。
但事实会让他们失望。有机农业作为一场社会运动,一方面出于朴素的对农业现代化的环境破坏的忧虑,另一方面则有一个鲜明的反垄断立场,与法西斯主义并无必然联系。所谓“有机”是农业与自然、农业经济与社会之间的“有机”联系。现代有机农业运动的早期鼓吹者之一阿尔伯特·霍华德(Albert Howard)发现,一战后源自炸药过剩产能的氮肥泛滥,严重破坏农田土壤,因此提倡以有机质堆肥还田取代氮肥,以保存地力。他在1940年的著作《农业证词》(An Agricultural Testament)中,将土壤称作一个国家真实而永恒的资本,既创造生产力,也需要经营维护。在美国,有机农业运动和60年代的反主流文化运动结合在一起,它反对现代农业对化石能源的依赖(生产化肥、长距离运输等),进而反对掌握化石能源的“军队-企业复合体”。在第三世界,巴西的生态农业(agroecology)运动旨在回应该国外向型种植园经济对农民的剥夺。世界各地的有机农业运动(不同的地方标准不同,名称也不同,但基本观念一致,这里只是泛称,也可以叫做“生态农业运动”、“可持续农业运动”)还都强调维护农作物的遗传多样性,反对整齐划一的商业化种子抹杀由千百年的选育种换来本土品种抗逆性及其品种的丰富性。
有机农业运动根本的诉求是生态环境保护和食物经济的民主化,被商业劫持而异化的伪有机,则另当别论。作家迈克尔·波伦在《杂食者的两难》中曾对这些被他称作“大有机”的有名无实者进行过批判。
源自鲁道夫·斯坦纳人智学思想的生物动力农耕(biodynamic agriculture)是最早的有机农业运动之一,前文提到它曾启发过纳粹农业部长达里。如今,生物动力农耕在德国有机农业界依然占有极高比重,它在强调呵护土壤肥力、善待牲畜、遵守耕作时令的同时包括一些玄奥成分,是一套不科学但能有效规范生态实践的知识体系。斯坦纳人智学中的种族主义思想一直为人诟病。2002年,生物动力学农耕的认证机构德米特国际在其章程中禁止了参加种族主义组织或与之合作者的加入。当今的德米特成员,绝大多数都区别对待斯坦纳的种族主义思想和生物动力农耕积极的生态观,其中包括笔者曾经访问的左翼无政府主义青年农业公社成员。
新的可持续农业运动也有意识地拒绝法西斯主义的渗透。德国在2011年爆发了一场声势浩大的反对工业化农业的运动,名为“我们受够了!”(Wir haben es satt!),它集结了从左翼环保团体,到普通家庭农场主,到基督教会的各路社会力量反对工业化农业污染环境、损害农民和消费者利益、虐待动物,每年1月在柏林举行大规模游行,与推广工业化农业的柏林国际绿色周唱对台戏。被问及生态法西斯的问题,其成员告诉我这的确是个问题,所以每年的论坛上都讨论“绿中之褐”的话题,他同时给我看示威海报上的一行小字:“我们不欢迎纳粹和种族主义者。”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蒋亦凡。来源: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黄芩)
(作者:蒋亦凡。来源:澎湃思想市场。责任编辑:黄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