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黄金时代》剧照。图源:豆瓣
《黄金时代》剧照。图源:豆瓣
初识丁玲是在许鞍华的电影《黄金时代》里。电影里丁玲在西北战地服务团伸出手欢迎萧红的画面,让我印象深刻,那个时候的丁玲在我的印象里是个女战士,然而当时并不十分了解她。
直至今日,我读过的丁玲作品也不多,《太阳照在桑干河上》《也频与革命》《我所认识的瞿秋白同志——回忆与感想》,对她的了解大部分来自李向东和王增如的《丁玲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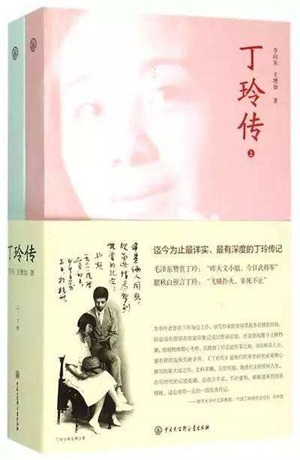
丁玲的一生可谓波澜壮阔和历经坎坷。看她的传记就像在跟一位朋友聊天,她把迷茫、转变、爱情、革命统统说给你听,她没有循规蹈矩度过无聊的一生,也没有选择一条完全看不到未来的道路。
一
从最初在上海认识瞿秋白到在延安见到毛泽东,丁玲实现了从一个“被恋爱苦着”的知识分子到“如何写好工农兵的”战士的蜕变。与大多数青年人一样,丁玲在寻路,在不断地转变。她初到上海就结识了共产党员,后又当面膜拜过鲁迅,更是见过白色恐怖,进过国民党的监狱,最后终于去了延安,使革命的“写作”成了可能。纵观丁玲的一生,归结到一点,即她是要革命的。
1922年,初到上海平民女校的丁玲就接触到陈独秀、恽代英、柯庆施等共产党员。但是那时她的主要目的是“学最切实用的学问”。开始,她充满新鲜感,好奇地观察,拼命吮吸。她跟着共产党员张秋人去浦东纱厂讲演,背着竹筒为罢工的女工沿街募捐,马克思诞辰纪念会她去听李汉俊讲演,无政府主义者开会也去参加。丁玲回忆说:“我们什么都接触,什么都吸收,只要是新的东西,我们脑子里并不懂得什么是马克思主义,什么是无政府主义,蔡和森也跟我们谈过,要我们去参加共产主义青年团。我‘对这些事情满有兴趣,认为这是革命。’”关于什么是革命,是丁玲一直探寻的问题。

丁玲像瞎子摸鱼一样寻找出路,却没有得到结果,还与共产党失之交臂。其中缘由,她回忆说:“首先,共产党当时只是一个不起眼的弱小组织,共产主义也不是唯一的选择。当时各种学说流派很多,冰之就曾参加过无政府主义组织的活动,我的朋友周敦祜(女),她有无政府主义思想,给我们拿过小册子看,我觉得他们很自由。那时有人说我和王剑虹有无政府主义思想。我们不参加共产党,也不参加青年团,那个组织也不是,我们不想要人管,只想自由自在。在迷茫中探索人生道路。”
多年以后在北京,她却怀念起那些共产党员了。但是一个也找不到了。从那时起,丁玲又开始写起了小说。她的小说充满了个人孤独灵魂的倔强挣扎和对社会的鄙视。《梦珂》、《莎菲女士的日记》便是她那时的作品。她自己说过:“我那时为什么写小说,我以为是因为寂寞,对社会不满,自己生活无出路,有许多话要说出来,却找不到人听,很想做些事,又找不到机会,于是便提起了笔,要代替自己给这社会一个分析。”而时至今日,青年人再一次感到了孤独和迷茫,想必后之视今,亦犹今之视昔,谁又不是呢?
二
与胡也频在一起的日子里,丁玲对革命愈加着迷。丁玲在《也频与革命》里回忆胡也频时写到:“回溯他的一生,想到他的勇猛,他的坚强,他的热情,他的忘我,他是充满了力量的人生啊,他找了一生,冲撞了一生,他受过多少艰难,好容易他找到了真理,他成了一个共产党员他走上了光明大道。”胡也频的进步促使了丁玲也在不断进步。丁玲说也频有一个很大的优点“那就是他知道了,认识了,就身体力行,勇敢的冲上去。也频没有许多知识分子夸夸其谈、轻视实践的通病,只要革命需要,他就愿意当马前卒,冲锋陷阵。”革命就是如此的简单有趣,远比坐在书桌上幻想日常精彩得多。
 丁玲与胡也频
丁玲与胡也频
郑振铎曾经说过:“凡是认识也频的人,没有一个曾会想到他的死会是那样的一个英雄的死。”胡也频被捕得时候丁玲直接或间接找了蔡元培、邵力子,甚至陈立夫。但是因为蒋介石直接过问,这些努力最后都石沉大海。据说当时沈从文见了陈立夫,回去告诉丁玲:“陈立夫把这案情看得非常重大,但他说如果胡也频能答应出来以后住在南京,或许可以想想办法。”“这是办不到的,也频决不会同意,他宁肯坐牢,死,也不会在有条件底得到自由。我也不愿意他这样。”这是丁玲的回应。两年以后被捕的她更是同样如此面对国民党的威逼利诱。1931年2月7日夜半,用机枪扫射,“左联五烈士”集体被枪杀于龙华司令部内之荒地上,尸体就地掩埋,不留痕迹。据淞沪警备司令部附近居民当时从楼窗目睹者说,临行时,他们从监门口起高呼着“共产党万岁”的口号,声震四邻,直至枪声止而喊声才息。
胡也频的牺牲使丁玲陷入了悲痛。但是丁玲没有吓到,而是化悲痛为力量,她拿起了笔,她要抒这巨大的苦痛。《一天》是胡也频去世后丁玲第一篇真正意义上的小说,写出了革命的艰难和革命者面临的困难。刚刚离开大学的21岁青年陆祥,住到沪西工人区去发动工人,这里的场景不再是《一九三〇年春上海》拥挤混乱而嘈杂的书房、客厅、商场、咖啡馆、电影院,而是拥挤混乱而嘈杂的工人居民区,陆祥的工作,也完全不同于若泉、望微那种飞行集会滔滔演讲轰轰烈烈的模式,而是深入下去,工人区的“种种生活于他实在不习惯”,工人不信任他,不欢迎他,辱骂甚至驱赶他,而他“为了一种自觉,一种信仰,”并不气馁。小说结尾,陆祥决定“写出这时期的一段困难的工作,而尤其应该表现出的,是一种困难之中应有的,不退缩、不幻灭的精神”。而后参与左联工作,继而主编《北斗》,这一次,丁玲已经开始接受“组织”分派的工作,因而也是丁玲走出书斋投入实际工作的转折。她在晚年曾经说过:“1931年之前,我是小资产阶级知识分子”,1932年丁玲加入了共产党。
三
革命的第二天是知识分子喜欢谈的事情,他们总是想着革命胜利后的第二天早晨醒来之后应该做些什么。可是我看来看去,却没有看到他们如何走到第二天。在一个资本主义的大山面前,是在山的旁边几个人凿开一个洞在里面生活呢?还是一群人把山移走呢?在延安,丁玲看到了后者。“尽是些鸡毛蒜皮的:这里缺一个理发师;那里有一个战士的老婆来了,要找一间房子住;那里又要毛驴,去拖柴禾……”从认识社会到批判社会再到融入这个社会改造这个社会,这就是延安共产党人的革命生活。
 延安时期的丁玲
延安时期的丁玲
丁玲因为之前跟知识分子打交道多,初到延安一时还不能融入他们的生活,她还是喜欢跟知识分子待在一起。但是延安又给丁玲提供了改造自己、追求进步的环境。当时延安物资紧缺,中央开大会的时候毛泽东就号召边区军民“自己动手,生产自给”,在马列学院读书的丁玲也加入了开荒的队伍。她给楼适夷的信里说:“适夷,这真伟大,每天队伍出去,站在荒山上,可是回来时,就多成了被开垦的处女地,踏着那些翻开了的泥土,真有说不出的味。两个星期开了一千的多亩地,而我们还不停止工作和学习呢。”丁玲主动捡重活干,有意识的锻炼自己,而劳动也改变着丁玲。20世纪50年代初,她总结那段经历说,劳动“对我是新鲜的事,我从这里得到锻炼,得到愉快。当时也确有过一点比较深刻的回忆,而且深深的感到,幸而我有过那么一段生活,劳动和艰苦,洗刷掉我多少旧的感情,而使我生长了新的习惯。这种内部的、细致的,而又反映在对一切事物上的变化,只有我自己体会得到。当然这不能全盘归之于劳动,但劳动的确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
从上海到延安,在共产党的“圈子”里,丁玲无时无刻不在感受到一个充满先进性的集体对她的帮助,而正是这个集体的存在才会使她能不断的进步。包括争议很大的《三八节有感》和《在医院中》。两篇文章都批判了延安当时的很多问题。但是出发点还是小资产阶级思想,想象的很好,但是事实没有那么好,并且总是把问题看得单纯,看得简单。革命队伍里永远不可能十全十美,总是会出现这样那样的问题。“我们不但善于破坏一个旧世界,而且善于建设一个新世界。”出现问题就应该积极的去解决问题,而不是站在高墙上冷嘲热讽。“批评应该是严正的、尖锐的,但又应该是诚恳的、坦白的、与人为善的。只有这种态度,才对团结有利。冷嘲暗箭,则是一种销蚀剂,是对团结不利的。”这是毛泽东对批评者的态度。而后毛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则对丁玲的思想产生了更大的冲击,讲话使她懂得了上海和延安的区别,过去她是对延安看不惯,呼吁改变种种坏现象,现在她开始对自己看不惯,要改造自身了。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何思齐。编辑:赫贫。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作者:何思齐。编辑:赫贫。本文为激流网原创首发,如有转载,请注明出处。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