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一、辛亥后的复辟
辛亥革命结束了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专制统治,建立了中华民国。而在革命后,革命派思想出现分歧,孙中山让出总统位置,准备致力于经济建设;章太炎提出“革命军起、革命党消”的口号,开始攻击孙中山,吹捧袁世凯;战功赫赫的黄兴表示“事定后,解甲归农”;宋教仁与章派不同,积极主张政党政治,为组成一个大正常以实现政党内阁把革命性的“中华同盟会”改组为鱼龙混杂、良莠不分的“国民党”。而正当宋教仁游说东南,准备组织责任内阁时,却被袁氏暗杀。

袁氏在篡夺辛亥革命成果后,并不满足于大总统职位,开始要复辟做皇帝。在袁氏复辟的逆流中,昔日的维新派首领康有为扮演了急先锋的角色,试图通过尊孔复古的舆论为袁氏的复辟帝制鸣锣开道。1914年袁氏通令全国,一律举行祀孔典礼,翌年授意杨度、刘师培、严复等人组织筹安会,作为复辟帝制的御用工具。复辟派的主要观点有三方面:鼓吹“共和亡国论”、提出所谓的“君宪救国论”,以及抛出“孔教治国论”。
二、新文化运动的兴起
中国思想文化领域内尊孔复辟逆流的猖獗,引起了当时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的警觉、愤慨和不满。正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一场在中国近代思想史上规模空前的,以民主和科学为主要口号的反封建思想解决运动——新文化运动兴起了。

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拉开了新文化运动的序幕。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高举“民主”和“科学”的旗帜,提倡个人独立自尊的新道德,打倒封建主义的旧道德;提倡尊重现实,尊重科学,反对鬼神迷信打倒一切偶像崇拜。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把批判的矛头引向了封建制度的理论基础,提出“打倒孔家店”的口号,对孔子学说和尊孔思想进行无情的抨击。他们认为,孔教是君主专制的和帝制复辟的祸根和思想基础。李大钊说孔子是“历代帝制之护符”;陈独秀说“孔教与帝制有着不可离散的因缘”,并认为民主国家祭祀孔子,正象主张专制国家祭祀华盛顿、卢梭一样的荒唐可笑。在深刻揭示孔教与君主专制制度之同时,他们还把封建伦理的三纲五常同社会组织中的宗法家族制度与政治上的君主专制制度联系起来,作为三位一体的东西加以批判。指出,三纲五常是群主专制制度的理论基础,守法家族制度是君主专制统治的社会的基础。新文化运动是历史上第一次全面地、猛烈地、直接地抨击了孔子和传统道德,这在中国数千年的思想文化史上是划时代的。
三、新西文化论战之诸派之争
随着新文化运动的发展,引起了反动军阀和整个封建势力的极大恐惧,顽固保守的旧文人也开始对新文化运动进行反扑。这班封建文化卫道者大体上可分为三派:国故派、学衡派、东方文化派。
(一)国故派及其代表人物
1919年初创办了以“昌明中国古有之学术”为宗旨的《国故》月刊,与《新青年》等进步刊物对抗,因此被成为“国故派”。这些老的守旧派由于论调过于谬误,手法、语言过于迂腐,在思想界已经没有多少市场,变成了人们嘲笑的对象。其主要代表人物有辜鸿铭、刘师培、林纾等人。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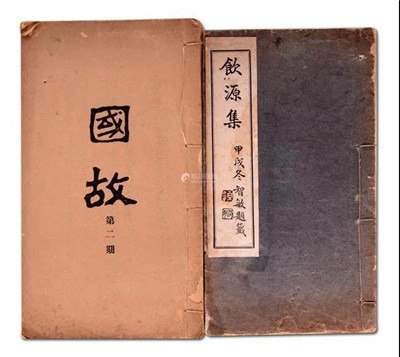
辜鸿铭(1857-1928),字汤生,他生在南洋,学在西洋,婚在东洋,仕在北洋,精通英、法、德、拉丁、希腊、马来亚等9种语言,获13个博士学位,像个留着辫子、穿着长袍马褂的假洋人,却是个地道的封建复辟派。他痛恨西人的殖民主义,也仇视民主共和制度,不时用古怪的言论为所有的传统中国伦理习俗而辩护。
刘师培(1884-1919),字申叔,生于一个今文学派的学者世家。1904年,他同其他同盟会作者一道创办了“国学保存会”,出版“国粹”学报,提倡“保存国粹”。1906年,他与一些中国学生在日本创办“天义报”,宣扬无政府主义。其后又变为复辟派,成为“筹安会”的“六君子”之一。此时刘师培把持了北大中国古代文学的讲席,考据和宣讲古代的旧制度和旧的伦理思想,抵制新文化运动。
林纾(1852-1924),字琴南,曾考中秀才和举人,但在京试中连年落榜。他三十多岁时已阅完四万卷左右的古书,成为清末著名的古文家兼画家。他在外语助手的协助下把西方小说翻译为文言文,成为当时中国多产的翻译家。在戊戌政变前,他就主张学习西方进行变革。但在辛亥革命后却以遗老自居,显露出顽固的封建意识。“五四”前夕,林纾记录里主张尊孔读经,攻击新文化运动,成为顽固的守旧派。
(二)“学衡派”及其代表人物
“学衡派”以南京东南大学的几个封建文人为中心组成。1922年1月,他们创办了《学衡》杂志,标榜“国粹”,攻击新文化运动。与国故派的老牌守旧分子略有不同,他们大都从国外回来,披的是欧洲资产阶级文化与旧中国封建思想拼凑而成的“新”装。其代表人物包括:胡先骕、梅光迪和吴宓等人。

胡先骕(1894-1968)颇能引用西方典籍来“卫护圣道”。《学衡》的宗旨“昌明国粹,融化新知”也正显示了这一特点。
梅光迪(1890-1945)发表的《评提倡新文化者》,以“学贯中西”自我标榜,对新文化运动倡导者极尽笑骂之能事,认为他们见识短浅,贬低他们所推崇的西方思想家。
吴宓(1894-1978)也把对西方进步思潮和社会主义学说的宣传诋毁为“专取外国吐弃的余屑”、“专取一家之学说”。
(三)东方文化派及其代表人物
东方文化派主要是指五四后以梁启超、梁漱溟、章士钊为代表的一批封建文化的鼓吹者,他们在“保卫东方文化”的借口下,试图用封建文化反对西洋文明,反对马克思主义。东方文化派是较高层次的论敌,他们不直接攻击西方文化,而试图证明西方文化不如东方文化,这就使东西文化问题之争演变为一场激烈的论争。
梁启超(1873-1929)在十九世纪末至20世纪最初的三四年间坚持倡导西学的改良主义,但随着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高涨,他迅速倒向维护旧统治秩序的一边。五四运动和中国共产党成立后更是成了反对马克思主义的挂帅人物。1920年他从欧洲游离回国后发表《欧游心影录》鼓吹西方物质文明破产,东方文化优越的论调。

梁漱溟(1893-1988),参加过中国同盟会京津支部,曾任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创办过山东乡村建设研究院。他于1921年出版的《东西文化及其哲学》,是东方文化优越论的代表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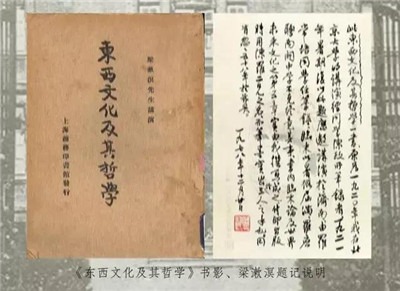
杜亚泉(1873-1933)是《东方杂志》的主编。他也曾含混地表示中国可以参考西方进行改革,但在《新青年》创刊后,他成为了新文化运动的重要论敌。1916年后,他发表了一系列文章,不同于老的守旧派简单的排外主义,他采取一种看似公允的姿态,做一些不可把两种文化比高下,只可“取长补短”之类的议论。实际上否认了中国文明有实行根本改革的必要,将封建文化糟粕作为国粹保存下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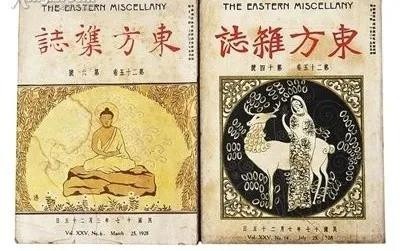
四、东西方文化论争的再展开
五四前后的东西文化问题论战,发生在大约1915到1925这十年间。这场争论的实质是中国封建旧文化和西方资产阶级新文化的斗争,也可以说是清末以来中学、西学之争的继续。对于论战内容的发展和重点的变化,大体可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东西文化能否调和?
这一阶段起于1915年《新青年》创刊至20年代初,论战内容集中于比较东西文明的优劣以及关于东西文化能否调和的争论。陈独秀的《敬告青年》一文,指出了东西文化的差异,他的总结的“六义”就是这种差异的体现;他把个人和家庭本位的差异放在最突出的地位,突出强调人的权利,激烈地抨击封建宗法制度。
针对陈独秀的比较,伧父(杜亚泉笔名)发表了一系列文章,想证明西方文化不如东方文化。他写西洋文明是“动的文明”,东方文明是“静的文明”,两者可取长补短,但不得不以“静的文明”为基础。他还主张以儒家思想为衡量是非的唯一标准,指责西方思想破坏了这种标准。伧父的观点是当时封建复古派在文化观念上的集中反映。
陈独秀、李大钊等人作为激进民主主义者,对伧父的挑战进行了针锋相对的反驳,表现出了与封建文化势不两立的革命精神,但言辞过于偏激,开了“全盘西化”说的先河。
1919年秋,东方文化派的伧父、章士钊又挑起了关于新旧思想能否调和的争论,“折衷”、“调和”意见一时蜂起。然而实际上这些一轮骨子里仍然坚持“中体西用”,最终目的仍然是要扼杀西方文化。
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积极应战,他们认为,旧文化和新文化是水火不容的,只能“以新代旧”,不能“以旧容新”。当时,陈独秀已经对“私有制下的旧道德”进行了一些分析,并没有简单地为西方文明辩护。李大钊更是运用唯物史观对新旧调和论思潮进行了批判,指出经济变动是道德变动的根本原因,中国的经济变动无可阻挡,新思想因而也是无法阻挡的。新文化运动的倡导者们虽然驳斥了新旧思想调和论,却并未科学地说明两者的继承关系;历史虚无主义的态度,也给复古势力留下可乘之机。
第二阶段:科学与玄学
第一次世界大战进一步暴露了西方资本主义腐朽,给东方文化派创造了天缘良机。他们不再在新旧调和上做文章,而是通过抨击西方文化的弊病,标榜东方文化的优越性。梁启超游历欧洲归来,发表《欧游心影录》证明西方物质文明“已经破产”;梁漱溟出版《东西文化及其哲学》一书,断言“世界未来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复兴”。
他们的反对者也发生了明显的分化,胡适等人仍旧坚持全盘西化的观点;而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为代表的马克思主义者举起社会主义大旗,确立了崭新的文化观。
紧接着,论战的中心又转到“科学的人生观”问题上,“现时代青年人应该有什么样的人生观才有助于国家富强和社会稳定”,即科学与玄学之争。梁启超、张君劢是玄学派(东方文化派)的主角,丁文江、胡适代表所谓科学派(西化论者)。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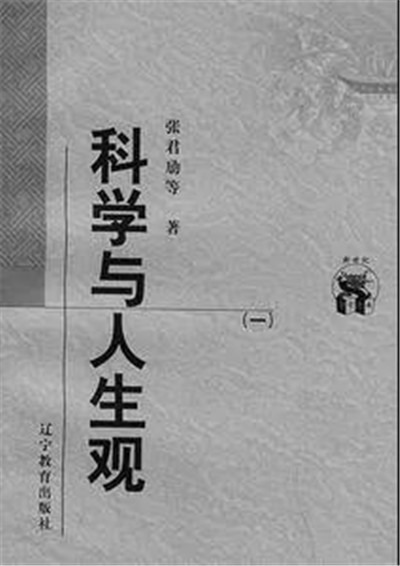
玄学派打着欧洲柏格森反理性主义的旗号偷运宋明理学,使论战蒙上了一层浓厚的哲学色彩。张君劢1923年于清华大学发表关于“人生观”的演讲,认为科学是客观的,人生观是主观的,人生观不能由科学所决定,人生观与科学不相容。他公然提倡孔孟至宋明理学家侧重内心修养的所谓中国精神文明,反对以人力支配自然的欧洲物质文明。梁启超同年发表《评新文化运动》一文,认为西学“所得者至为肤浅”,不到几年就造成“精神界大乱”,“物质有限而人欲无穷”,招致了严重的后果。
丁文江发表《玄学与科学》进行反驳,他认为“今日最大的责任与需要,是把科学方法应用到人生问题上去”,科学就是教育和修养最好的工具,它可以培养一个人平心静气追求真理的精神;他希望青年人能够警惕“玄学鬼”的诱骗,不能养成一种纯主观的、不明是非的人生观,这对我们的社会百害无一利。

陈独秀进一步要用“唯物的历史观”来作为基础建立科学的人生观。他指出科学派对玄学派的批评只是“五十步笑百步”,科学派在对“科学”的解释上也是非科学的,是马赫主义的主观唯心主义的变种。一味地说“科学的人生观”如何好,并不能解决问题,更重要的是用科学具体地解释玄学派所强调的“良知”、“直觉”等非理性的存在,才能真正树立起科学的人生观的权威。
科玄论战之后,马克思主义在青年中得到了更广泛的传播,马克思主义作为一种科学,日益为人们所理解、接受和信仰。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wind_1917
 (作者:沈亚宁、静穆。来源:实践社会科学。责任编辑:郭琦)
(作者:沈亚宁、静穆。来源:实践社会科学。责任编辑:郭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