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家、哲学家、社会活动家,陈玉平一生致力于服务和权利倡导。从在底特律进行社区活动,到领导民权运动,再到她那些让我们过着有意义生活的想法。作为中国移民的后代,作为一位女性,陈玉平很早就明白,这个世界需要改变,她克服一切障碍也正是为了改变世界。”
——美国总统奥巴马于2015年10月5日陈玉平去世当天发布的悼词

陈玉平,英文名格蕾丝·李·博格斯(Grace Lee Boggs),1915年出生于美国的福建移民家庭,纽约市中产社区长大,1940取得哲学博士学位,战后成为美国劳工与反种族主义运动的中坚分子,与丈夫詹姆斯.博格斯(James Boggs)一起领导底特律地区的黑人运动;20世纪后期,她是基于底特律的社区建设运动的领导者,也被美国亚裔社会运动者视为精神领袖。 2015年,陈玉平离世。纪录片《美国革命家:陈玉平的演进》( American Revolutionary: The Evolution of Grace Lee Boggs)讲述了这位传奇革命者的百年人生。为什么一位华裔知识女性的命运,会如此深刻地与美国黑人运动结合在一起?不少人抱着这样朴素的好奇走近陈玉平的生命与政治,从中得到的启迪却远远超越身份政治的范畴。
当边缘身份遇上革命浪潮
陈玉平的生命历程跨越国族、阶级、种族、地域,也打破性别与年龄的刻板印象,对于芸芸众生来说,着实是个传奇。但当我们把个人经历还原到历史语境中,会发现她的种种貌似偶然的道路选择,是与漫长二十世纪的革命浪潮和社会变迁环环相扣的。在十九、二十世纪之交的华人移民潮席卷下,陈玉平的双亲从广东汕头几经辗转来到美国,依靠开餐馆在美国东海岸扎下根来,成为纽约当地的“华人餐饮之王”,殷实的家境让陈玉平和兄妹们在美国白人中产社区度过少年时代。

世纪初的女权运动给女性带来接受高等教育的机会,这使得陈玉平作为一个女孩,有机会进入最好的女子私立大学巴纳德女子学院和布林茅尔学院研究生院学习哲学,并于1940年获颁博士学位。但彼时有限的平权成果也让陈玉平明白,作为华人女性,即便取得博士,也没有太多机会得到大学教职。
陈玉平在校园已经受到30年代经济大萧条和劳工运动的影响,开始对世界革命和左翼运动感兴趣。毕业后,她只身前往劳工运动蓬勃发展的芝加哥,打算以图书馆文员职位谋生并展开写作,却因女性有色人种的身份,在生活中屡次遭遇歧视。彼时的芝加哥黑人聚集,工人组织活跃,出身优渥的陈玉平虽是初次接触黑人社区,但内在的正义感和对自己边缘身份的敏锐反思,让她怀着极大的热忱投入了激进左翼运动——陈玉平的命运从此与社会革命紧紧相连。她在自传里说,“如果我不是女性,也不是美籍华人的话,就不会这么早地认识到社会需要彻底的改变。”
陈玉平革命者生涯的高潮,随着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际共产运动、第三世界国家独立运动和美国国内黑人民权运动的相继崛起而到来。在40年代,陈玉平加入美国社会工人党的“约翰逊-福利斯特派”,追随生于特立尼达的著名马克思主义后殖民革命家C. L. R. James,和同事们在工厂组织学习小组,撰写文章,大量阅读、讨论马列理论, 并逐渐发展出自己的革命理论。50年代初,她与志同道合的底特律黑人工人作家詹姆斯.博格斯结为夫妻,从此开始了扎根底特律的,长达半个多世纪的在地运动。
在60年代,陈玉平和伙伴们参与各种示威、集会,反抗种族隔离,在马丁·路德·金所主张的非暴力路线与马尔科姆·X主张的激进抗争之间,他们更同情后者的做法,认为黑人抗争的目标不应该是成为白人一样的模范公民,而是要夺取独立的政治权力。1967年,反抗运动在“底特律暴乱”中达到顶点。虽然彼时底特律和其他许多工业城市逐渐认可黑人独立政治力量,涌现出越来越多黑人市长、法官、校长,但随着美国产业转移海外,白人搬离市区,黑人不再被当作资本主义生产过程中的生产者而被需要,但又被开发成为消费者。街道上的年轻人处于一种“永无停止的叛乱状态,索要、抢夺财物”,他们对于白人至上主义的愤怒并没有机会转为建设性力量,有组织的政治反抗逐渐被失业、贫穷、毒品交易替代,整个社群充满危机。
当激进运动在70年代偃旗息鼓,世界政治转向保守主义,陈玉平意识到旧有的斗争方式已经不能在现实中持续
改造世界要从改造自己开始:一个革命者的反思
为什么希冀改造社会的运动最后会走向暴乱和道德崩溃?当旧制度瓦解,新权力登台,为什么却无法克服那些顽固的等级思维、压迫机制?是否存在一种不容质疑的革命理论,可以指导任何行动?在反抗者夺取了政治权力以后,应该如何应对社会、文化、道德层面的挑战?
陈玉平和伙伴们在革命退潮之后,仍不断思考这些问题。她的哲学训练中深受黑格尔哲学影响,也关注毛泽东等第三世界革命者“在斗争中建立”的革命策略。她认为不存在一劳永逸的教条,思想在与现实的张力中,应该不断进化。当夺取政治权力以后,革命最终应该落到社会和文化的层面。想避免以暴制暴和旧结构的复辟,革命者就要不断改造自己。 “要改变这个世界,我们必须改变自己”——陈玉平在自传里如是说。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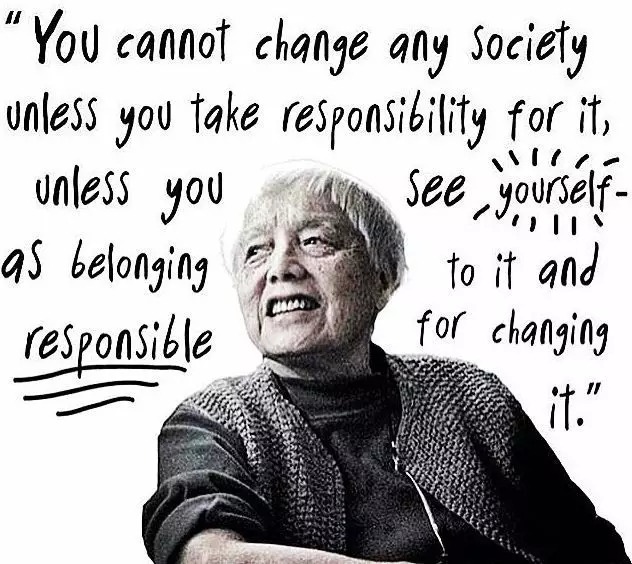
陈玉平生命的后五十年,把斗争的场域聚焦在社群与日常生活,致力于底特律的社区重建运动。她比年轻时更认同马丁.路德.金遇刺前两年的反思——在那些濒临死亡的城市里,年轻人应该投入到“直接自我转型以及社会转型的行动”中去。她与丈夫编写了《黑人革命党宣言》,呼吁黑人青年超越叛乱,强调组织中人与人之间的义务、责任 。陈玉平也特别吸纳了女权运动对科学理性主义、主-客观二元论的批判,挑战既有黑人运动中普遍存在性别歧视和官僚主义。
从80年代开始,陈玉平组织和参加了许多底特律当地的社会组织,回应具体的妇女健康、家庭关系、环境保护、青少年教育、老年人福利问题,重新探讨人与人之间如何建立长久、信任的关系。1992年,陈玉平发起了“底特律夏天”运动,吸引青年志愿者,一砖一瓦、一树一木地改造颓败的城市社区。几十年来,他们把空地变成儿童公园、瓜果基地,把废屋变成自行车俱乐部、图书馆。
陈玉平曾说:
“当我们走进21世纪时……如果我们想减少犯罪、暴力、流浪、癌症和低出生率等问题的话,就必须创造机会去解决它们。我们不能让那些跨国公司去做这些决定,它们不再忠诚于我们的社区或国家——也不能依赖政客们,他们只为这些公司服务……这些问题是没有快捷或简单的答案的。20年前,‘黑豹党’说,‘如果你不是解决问题的一部分,你就会是问题的一部分’。成为了‘底特律夏天’的志愿者,你就已经成为解决问题的一份子了。”
晚年陈玉平:现在到了重新筑梦的时候了
陈玉平晚年,亚洲移民二代在美国成长起来,有不少亚裔青年视她为自己族裔的运动楷模,从各地来“朝圣”;陈玉平也乐于与各种人对谈,各地巡讲,分享她在早年也许没有来得及思考的自己的亚裔女性身份。有一次,当被一位亚裔年轻女孩问起作为社区建设运动的领导,如何抵御困难挫败带来的枯竭、疲惫感时,陈玉平说:“我想这跟我在一个地方待了55年有关,我要为它负责,因此我不会感到枯竭。”
虽然陈玉平的生平可以从多种角度解读,但中国社会对她的关注,的确源自其另类的美国革命者身份。陈玉平作为一个葛兰西意义上的有机知识分子,把一生融入到了看似与她的阶级、种族、甚至性别都不必然相关的社会运动。偶然性背后,似乎也显现出她的边缘身份与大时代浪潮撞击后的某种必然。
今天的中国青年,比以往任何历史时期,都更积极地回应着全球资本主义和国家体制对个人社会身份的召唤,我们自觉而热忱地询问自己,在今天,如何做“中产”、“爱国主义者”、“女权分子”或者“左派”……陈的故事在提醒我们,身份的命名和辨识本身是一个政治过程,没有一劳永逸的答案。超越固定、狭隘的认同政治,社会才有走的更远的可能。而这种超越的动力,除了大时代的力量,也在于每个有志于改造世界的人,是否有改造自己的智慧与勇气。
(作者:董一格。本文来源:“女权之声”公众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