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人境》评论专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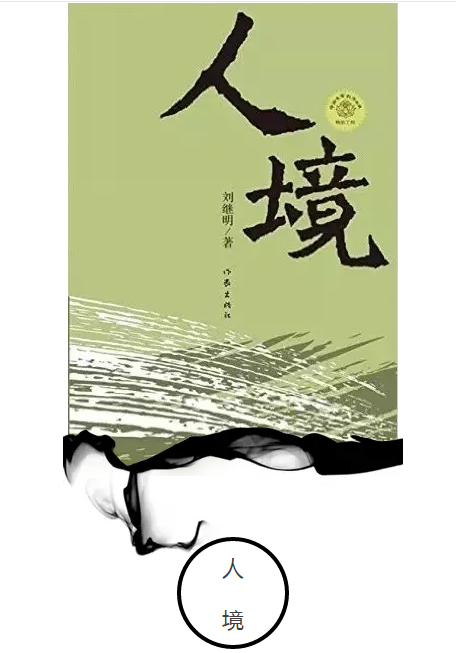 刘继明著 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刘继明著 作家出版社2016年版
【编者按】本文作者张慧瑜认为,《人境》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就是试图重新书写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做一个总体的评价。相比80年代以来重写20世纪历史或者当代史的长篇小说,《人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反思历史的历史感,通过对80年代重写革命历史的再反思,把50年代到70年代重新叙述为新时期的精神资源;二是反思现实的现实感,借助对80年代所形成的新启蒙价值和发展主义理念的批判,重建全球化时代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社会图景。可以说,《人境》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尝试整体性地回应当下中国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困境。
我们如何理解《人境》?
 张慧瑜
张慧瑜
刘继明的《人境》是一部非常重要和特殊的书。正如陈福民先生在《人境》研讨会上所说,对于新时期文学来说,有没有这本书很不一样,有这本书,新时期文学要丰富一些,没有这本书,则要单调许多。
《人境》有一个很大的野心,就是试图重新书写新时期以来的历史,对这段历史做一个总体的评价。相比80年代以来重写20世纪历史或者当代史的长篇小说,《人境》有两个突出特点,一是反思历史的历史感,通过对80年代重写革命历史的再反思,把50年代到70年代重新叙述为新时期的精神资源;二是反思现实的现实感,借助对80年代所形成的新启蒙价值和发展主义理念的批判,重建全球化时代中国从乡村到城市的社会图景。可以说,《人境》采用现实主义的叙事策略,尝试整体性地回应当下中国的社会危机和精神困境。
我想从小说的主题、结构和风格这三个角度来理解《人境》。
一、何为“人境”?
《人境》的名字借用于东晋田园诗人陶渊明的诗“结庐在人境,而无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人境”是指一种既在人间,又“无车马喧”的悠然状态,也就是追问一种人的境界或人间的状态。这让我想起80年代初期对于人性、人道主义的讨论,如戴厚英的《人啊!人》、路遥的《人生》等作品。这部小说在重新回应80年代之初的人道主义的问题,也是中国革命、现代性的基本问题,就是塑造什么样的人、什么样的人性、人格的问题。就像小说的主角马垃引用《安娜·卡列尼娜》中列文的话,“要是不知道我这人是什么,我活着为了什么,那就无法活下去。可是我无法知道,因此无法活下去”[1]。之所以会有这样的困惑,是因为生意失败、锒铛入狱的马垃对80年代以来引领自己的文化精神产生了怀疑,这迫使出狱后的马垃返回到故乡神皇洲,而他的哥哥马珂的初恋情人、大学教授慕容秋最终也回到了这个地方。
马垃和慕容秋是《人境》的核心人物,整个故事都围绕他们来展开。小说接近结尾有这样一段话,“那场大火发生后,亲爱的慕容姐姐如遭雷击一样垮了下来,很长一段时间面如死灰、萎靡不振,我预感到在她失去爱情的同时,我们也将失去她。这是一种无法逃避的宿命,对个人来说是如此,对整个神皇洲来说也是如此。两个月之后,毛主席就逝世了。全村的人和孩子都哭了;……这一年,我的心智和身体仿佛停止了发育和生长。我成了一个永远长不大的孩子”[2],哥哥的去世、毛主席的逝世,使得马垃永远停滞在那里,拒绝成长。这段话下面是慕容秋看到哥哥的墓碑说“请原谅我现在才来。这么多年,我一直没有勇气面对这块墓碑。因为它不仅埋葬了我的初恋,还埋葬了一个时代”,哥哥的死也使得慕容秋停留在那个时代,就像马垃像个少年,一直没有结婚,慕容秋也是如此,离婚后一直没有再婚,他们为了保持精神上的纯洁,带有某种“禁欲”的色彩。这本书写的就是这样两位“不忘初心”的、永远停留在少年少女时代的人的精神史和社会史。
二、小说的结构
《人境》分为上下两部,上部是马垃的故事,下部是慕容秋的故事。看起来像两个平行故事,前者是新世纪以来的新农村建设,后者是女教授的学术反思。这两个故事又有内在的关联,首先哥哥马坷是马垃和慕容秋共同的精神偶像,马坷是共产主义战士,是农村人民公社的基层干部,其次,马垃所从事的新农村合作社和慕容秋所关心的国企工厂改革都与辜朝阳有关,这是他们共同的敌人,辜朝阳是资本和外国资本的代理人。在我看来,这样两种农村和城市的故事是为了回应80年代以来关于农村和城市的主流叙述。
80年代在从革命向启蒙、现代化的转型过程中,出现了两种乡村叙述。一种是愚昧、落后、静止的地方,是等待现代化的地方,农村从组织化的、集体经济的人民公社重新回到了自然经济的状态,农民也变成了五四时代的阿Q和闰土,这成为80年代最主流的农村叙事,当然,农村也确实在80年代中期所启动的城市改革和90年代的现代化中变成了被遗弃的空间;第二种是诗意的、神性的、野性的、史诗的、抽象的、审美化的田园,这在一些寻根文学和知青文学中可以看到,把边疆、插队的地方变成“我的遥远的清平湾”,最典型的还是海子的诗,海子对土地、麦田的书写完成了对乡村的史诗化和去历史化。
这样两种乡村故事有一点是一样的,都是去革命化的、非历史化的乡村,也是非现代的、非工业化的乡村。换个说法,是现代性视野下的两种乡村叙述,一个是愚昧又落后的前现代,一个是乡愁、田园诗和精神家园。这种乡土叙述一方面完成了乡土的去魅化、去历史化,另一方面又完成了再神化、抽象化和神秘化。这种自给自足的乡村空间又演化出两种乡土历史,一种是乡村变成了有儒家传统的、民间信仰的相对独立的乡里空间,不管是土匪、军阀、国民党、共产党,都是外来者,早晚有有一天会离开,唯一不变的是固有的乡村秩序,如陈忠实的《白鹿原》就是如此;第二种是没有历史的循环史观,除非莫言的《红高粱》中“日本人说来就来”,乡村才进入历史,或者像刘震云的早期中篇小说《头人》所写那样,这是一个乡长变保长、保长变支书的循环往复的乡村历史。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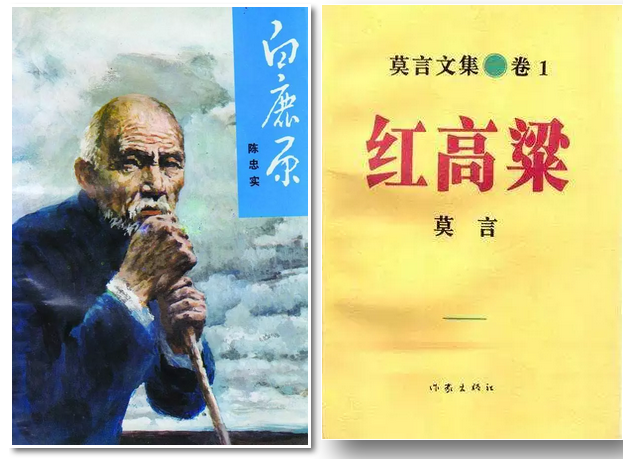
《人境》与这种80年代乡土叙述不同,在上部出狱后的马垃2000年返回神皇洲时,看到的是一个凋敝的、衰败的乡村,于是马垃开始用合作化来实现乡村自救的实验。这种乡村叙述延续了社会主义现实主义的农村题材传统,是一种以乡村为主体的叙述方式。马垃所进行的农民专业合作化实验有这样几重意义:首先,合作化是改造人,赋予人以生活的价值和尊严的过程。面对90年代农村的人员流失、土地抛荒现象,马垃带领老弱病残重新组织起来,如谷雨是受伤后返乡的农民工,他加入合作社后说“如果在城里,他只不过是一个比稻草还要轻的民工,跟一只蚂蚁和一条狗差不多,就是死了也不会有人瞭一眼,也只有在茴香心目中,他才是个有分量的男子汉。这让他感到了些许做人的尊严;这种做人的尊严,也只有在这块生养他的土地上才可能获得”[3]。还有对小拐儿的收养,让他学会种地,开始新的生活,逯永嘉的女儿唐草儿也在合作社里戒了毒,也就是说合作社是拯救人的地方;其次,合作社重组了溃败的乡村关系和社会关系,让被城市化所掏空的乡村恢复了生机,如以合作社贷款的方式解决了庄稼地灌溉系统和农户饮水问题、过年时组织了舞龙队、舞狮队,恢复了乡村文化,也就是说合作社不只是解决经济问题,也是政治和文化秩序的重建者;再者,马垃的有机大米合作社与种粮大户赵广福的转基因棉花的竞争,是当下农村两种发展道路的对立,一是有机农村、保护环境,但依靠城市消费,二是依靠大资本、外国资本来发展农村;最后,马垃所办的农业种植和销售专业合作社是经济合作社、公司合作社,与毛泽东时代的政治合作社不同,后者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要建设一个现代化的、集体化的、没有剥削的农村,而前者更像是一种对被抛弃的乡村的自救行为,因此,也是注定会失败的。
在下半部慕容秋的故事里,《人境》在与两种城市故事进行对话。一是对厚黑、权斗式的官场小说的反思,这种官场小说把政治理解为一种权力斗争,而不具有政治性的含义,《人境》则呈现了各级官员、革命二代、外国资本之间的利益勾结,这种官、商、学的利益共同体(政府招商、外国资本支持、学术界呐喊)是造成国企工人下岗、企业污染的根本原因;二是对严歌苓、王安忆式的家族史的反思,慕容秋与逯永嘉的父辈也是一种带有民国范儿的故事,但《人境》中让唐草儿把姨太太的小洋楼改造为一个教育中心,而没有成为民国范儿的继承人。
三、现实主义风格
《人境》是一部带有现实主义风格的小说,塑造了典型环境下的典型人物。首先,《人境》是多种人物、多个声部,也是高度象征化。马垃像个游历者,他一方面回到神皇洲寻找历史,找到哥哥马坷的遗物,一本日记本和小说《青春之歌》,另一方面又让各种人物打开心扉,讲出他们的心里话。小说中的很多人物都有一个小传,也就是来龙去脉的历史,尤其是让80年代以来被压抑的老支部书记、老革命、老右派如郭东生的父亲郭大碗、慕容秋的父亲慕容云天、丁友鹏的父亲丁长水等重新发声,表达他们对现实的不满,还有国企工人陈光对国企改革的不同声音以及新一代大学生如鹿鹿投身于社会运动。不过,在这些如此众多的角色中,有一个角色始终无法开口,这就是那只叫“社员”的狗,这本身很具有象征性,社员的名字本身带出了人民公社的历史。也就是说随着社会主义农村实践的失败,作为实践主体的“社员”也难以讲述自己的历史,这显示了80年代以来的主流叙述对革命叙述的压抑。
其次,这部小说有丰富的社会面,呈现人物关系背后的经济动力,从上到下、从高层到底层,不光从一种道德上的好人与坏人,而是把人放在不同的经济关系中来理解。《人境》表现了三代人的情感经验,父亲一代如郭大碗、慕蓉云天、丁长水、辜烽等要么是革命的参加者,要么对革命保有同情的态度,而郭东生、丁友鹏、辜朝阳等子一代则变成官倒、资本家和发展主义的官员,第三代小拐儿、唐草儿、鹿鹿等又有他们自己的遭遇和新的选择。
其三,我认为 《人境》的现实主义比《创业史》、《艳阳天》的格局更大,因为社会主义现实主义有一个不用说出来的“政治正确”的前提,就是社会主义国家制度和公有制的经济基础,这是《创业史》和《艳阳天》无需论辩的前提。而《人境》则是在社会主义解体、失败的背景下,在中国加入全球化的背景下,从中国农村到美国华尔街都有直接关系的全球结构下来叙述历史。
 很多论者把马垃当作一个“新人”形象。那么,马垃究竟是新人还是旧人呢?马垃身上流淌着共产主义战士马坷和自由主义精神导师逯永嘉的双重血脉。如果说马坷是牺牲者、受难者,那么逯老师则是欲望、尼采和商人的化身,前者是大公无私的、为了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甘愿做一砖一瓦的共产主义战士,后者是追求自由、成为超人、强者的浮士德,是资本和权力的象征。马垃想同时继承这两个人的衣钵,把他们埋葬在一起,可是这样两个精神支柱本身是激烈冲突的,因此,马垃带有两面性,也必然是矛盾的。相对辜朝阳、丁友鹏、李海军来说,马垃是新人,是具有新的思想和情怀的人,但马垃也是一个旧人,因为革命之后的岁月回到革命之前,马垃有一颗19世纪的心灵,那个带风车的房子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此,马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种有机农业的合作社是一种弱势群体的自我拯救,无法抵抗权力与资本汇集的洪水的力量。《人境》正是用这种失败来呈现这个时代的绝望感和无力感的。
很多论者把马垃当作一个“新人”形象。那么,马垃究竟是新人还是旧人呢?马垃身上流淌着共产主义战士马坷和自由主义精神导师逯永嘉的双重血脉。如果说马坷是牺牲者、受难者,那么逯老师则是欲望、尼采和商人的化身,前者是大公无私的、为了集体利益牺牲自己,甘愿做一砖一瓦的共产主义战士,后者是追求自由、成为超人、强者的浮士德,是资本和权力的象征。马垃想同时继承这两个人的衣钵,把他们埋葬在一起,可是这样两个精神支柱本身是激烈冲突的,因此,马垃带有两面性,也必然是矛盾的。相对辜朝阳、丁友鹏、李海军来说,马垃是新人,是具有新的思想和情怀的人,但马垃也是一个旧人,因为革命之后的岁月回到革命之前,马垃有一颗19世纪的心灵,那个带风车的房子本身就是不现实的,因此,马垃的失败也是必然的,这种有机农业的合作社是一种弱势群体的自我拯救,无法抵抗权力与资本汇集的洪水的力量。《人境》正是用这种失败来呈现这个时代的绝望感和无力感的。
注释:
[1] 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6月,第100页。
[2] 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6月,第479-480页。
[3] 刘继明:《人境》,作家出版社,2016年6月,第159页。
(作者:张慧瑜。本专辑评论文章刊发于《长江丛刊》2017年3月上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