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苦劳网按】按美国时间,今日是九一一恐怖攻击第十八周年。也就在日前,世界体系理论大师沃勒斯坦逝世。本文是世新大学社发所教授陈信行于沃勒斯坦2001年访台后所写,评述了沃勒斯坦、纪登斯、贝克、福山等西方公共知识份子于九一一事件前后的评论与社会理论。原文载于2004年《世新人文社会学报》第五期,苦劳网获得作者授权后刊载于此。
 《现代世界体系》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图片来源:Brennan Cavanaugh/Flickr)
《现代世界体系》作者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图片来源:Brennan Cavanaugh/Flickr)
2001年九月十一日美国纽约世贸大楼与五角大厦的恐怖攻击事件之后,从许多面向上看来,世界似乎进入了一个全新的纪元,前此一切关于国际政治、关于安全、关于发展的规律与价值都必须受到挑战。乔姆斯基──英语学术界最著名的政治异议份子──坦率地说出欧美主流所受到的震撼之大:
近五十年间美国在世界大半个地区动辄诉诸武力,受害者不计其数。头一次,炮火转向美国,这的确是剧变!对欧洲来说也一样,甚至这转变显得更为剧烈。……除了极少数的例外,他们不曾遭到来自外国被征服者的攻击。英国没被印度打过,比利时没被刚果打过,义大利没被衣索匹亚打过,法国也没被阿尔及利亚打过。(Chomsky, 2001: 12-13)
因此,至少在人民受到暴力威胁的恐惧这点上,911事件标志着150年来世界潮流的逆转。自十九世纪中期的帝国主义时代以来,中心国家的社会一般说来不需面对其他地区人民普遍遭受的征服、战乱、与掠夺;如果有,祸乱必然是来自其他强权。因此,强权之间的稳定平衡,大致就能够保障中心国家的安全,而把层出不穷的悲惨乱象限制在所谓的第三世界。而从911事件开始,这个局面被打破了!
尽管如此,二十世纪末以来的媒体阅听经验应该早就让成熟的阅听人培养出一种对新闻事件的历史重要性保持审慎狐疑的态度;毕竟「划时代」、「历史性」的时刻几乎无日不在追求戏剧性效果的晚间新闻与广告版面中出现,而人们的生活经验却通常保持着某种连续性。绝大多数比较成熟的社会理论,在试图捕捉连续性的结构发展与变迁时,通常选择较长期的时间向度作为分析的尺度,从而倾向于把偶发的、短期的、在特定历史时空下发生的「事件」──即使是造成重大断裂经验的事件──视为次要的、衍生的(derivative)。这种倾向时常会牺牲了对于时势(conjuncture)的分析能力,从而对于应对时势的策略较为缺乏。
伊曼纽尔‧沃勒斯坦对911事件的态度乍看之下类似这种「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的世故。在2001年于台北的研讨会中,他说:「我的估计是:历史会证明,911事件只是一个小插曲、一个泡沫。」其实不然,在更大的层次上,沃勒斯坦眼中的二十一世纪初,将出现一个更巨大的危机,其规模与深度之惊人,使得连911这么耸动的事件,相形之下都将显得无足轻重,因为,「五百年的资本主义即将终结」!
在诸多分析当下社会变迁理论的光谱上,沃勒斯坦的命题或许属于最大胆的一端,其所使用的时间尺度是最大的。然而,当前的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正处在危机当中,这却绝不是少数人的危言耸听。911事件及其后续的腥风血雨不过是这个危机时刻最暴力的面向之一,地缘政治上的凶险不过是在2000年底以来风雨飘摇的世界经济体系上再投下一个变数。如果美国的新经济泡沫的崩溃与日本的持续的经济衰退还不足以说明问题,2001年底,阿根廷的经济崩溃则绝不含糊地显示了危机的严重性。而同一段时间爆发的美国「新经济」模范生恩隆公司的倒闭则如滚雪球般卷进愈来愈多的资本主义中心国体制败坏的黑幕,严重地威胁到其政治经济体制的正当性,更令人质疑新经济的真实性。我们甚至可以预期,类似的冲击还会接连在各个角落爆发。而自1990年代中开始,跨越穷国与富国界线的、以「反全球化」为名的社会运动更让这些体制危机的政治冲击无所隐藏。
危机的存在是一回事。然而危机的性质是什么?是根本问题还是一时失衡?分析危机的适当时间和空间尺度是什么?这些却是需要追索的课题。沃勒斯坦的命题是关于当代危机的诸多辩论与探索中的一家之言。本文尝试简述沃勒斯坦所身处的西方世界知识圈的几个公众知识份子(public intellectual)关于当前危机的论述,以勾勒出一个简单的论述地景,让国内读者比较周全地理解并评估他的分析。我的叙述集中在近年来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以及全球化论述的中心课题──「现代性」的问题以及民族国家作为分析与实践的单位的有效性等等。关于这些课题的争论车载斗量、难以尽述。1。在此,我只能选择性地挑出几位论者,分别代表右翼保守主义(如亨廷顿与福山)、试图超越左右之分的中间派(如贝克与纪登斯)、和包括沃勒斯坦在内的广义的左翼。我认为,对于重大历史事件的解读是理论的试金石,因此我主要集中在这些论者对于911事件及其前后的世界局势的变化,再由他们的时势分析来检视其理论立场,并讨论理论的取径如何与政治立场相互影响。
「历史的终结」抑或「文明的冲突」?
911事件发生之后几个月,台湾与国际主流媒体一致把美国右派大师亨廷顿(Samuel Huntington)1993年出版的「文明的冲突」高举为中心议题。据亨廷顿所述,冷战结束后的世界冲突非但不会消减,反而可能愈来愈尖锐、愈无可转圜。资本主义与社会主义阵营四十余年的冷战不过是在同一个普世架构下对于不同世界发展路径的斗争,而后冷战时代的冲突却是「西方」、伊斯兰、东亚等不同「文明」之间千年缠斗的继续,事涉文化认同与种族之争,必难善罢。
到底「盖达」集团恐怖份子与美国的冲突是不是「西方文明」与「伊斯兰文明」之间的冲突?这种冲突是否当真是你死我活,没有转圜余地?这些课题在911事件之后占据了诸多辩论的空间。然而,值得玩味的是,在亨廷顿之前,当老布希初任美国总统,冷战正在划下句点的时候,另一位美国右派大师风行一时的说法似乎恰好否定了亨廷顿的悲观主义。
法兰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在1989年出版的《历史的终结》中提出来的命题,十余年来以各种面貌出现在关于「全球化」的论述中。福山认为,苏联集团的瓦解代表了前此所有历史的终结;西方所代表的民主政治、自由市场已经大获全胜,法西斯主义、社会主义和「所有的威权主义」都不可能再提供任何另类出路(Fukuyama, 1992: 152-157)。但是如戒严时期的台湾一般亲资本主义的威权主义例外,不止是打着阶级斗争之名的东西阵营对抗已经结束,福山认为,战后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关注的「南北矛盾」的提法也已经过时。他认为,从列宁以来对帝国主义的批判,尤其是战后拉美兴起的依赖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也可算做其中一支),已经被包括台湾在内的东亚四小龙的兴起证明是错误的。四小龙的例子证明,对跨国资本的抵抗是无用的,心悦诚服地加入资本主义国际分工,反而能飞黄腾达(Fukuyama, 1992: pp. 122-135)。
英国柴契尔首相著名的口号「TINA」(别无出路 There Is No Alternative)即是福山命题的体现,1980年代开始的新自由主义浪潮也据此而宣称,无论在任何国度、任何政治、经济、文化情境中,唯一可行的道路是经济自由化、私有化、去管制化、全球化;换言之,即服膺于据说已经被历史证明的信条。以前被认为具有无比重要性的民族国家之间的差异,以及相应着这些差异的国家主权问题,在历史终结之后,变得愈来愈不重要。许多全球化论者(例如日本企业家大前研一)因而大胆地主张:民族国家已经终结了。全球自由市场将瓦解所有的界线(Ohmae, 1994)。
911事件一清二楚地向资本主义中心国的人们显示:1989年之后的世界,绝不是资本主义式的世界大同。因此,911隔天,英国《泰晤士报》的一篇具名评论就指出,「文明的冲突」已经取代了「历史的终结」成为21世纪西方的新挑战,而这将比冷战还更凶险。即使在冷战顶峰的古巴飞弹危机中,甘乃迪还可以和赫鲁雪夫通热线电话,而现在,美国的敌人无所不在,随时伺机而动(Hames, 2001)。柯林顿时代关于全球化的各种乐观赞颂可以休矣。
福山本人在《华尔街日报》上的回应很能够代表英美右翼的观点(Fukuyama, 2001)。他认为,西方民主与资本主义所组成的「现代性」(Modernity)仍然坚强、仍然是唯一的出路,从世界各国纷纷选择这条道路、各国人民争先恐后要移民到欧美国家就是明证。亨廷顿之说的可取之处在于指出各种不同文化对于现代化有不同的适应能力。基督教文明本质上比较适应民主,而伊斯兰文化显然是比较适应不良的,因而会产生许多恐怖份子。但是,激进伊斯兰绝不能取代西方文明、取代「现代化」。冲突或许还会存在,但是这是落后与进步、消失中的传统与上升中的现代文明的冲突。
如福山所述,「历史的终结」与「文明的冲突」两个命题之间的矛盾是次要的。双方都同意,资本主义西方的一切都代表光明进步,而反对它的所有人都代表黑暗落后,必须也必将被扫进历史的灰烬中。他们不同意的只是西方的全盘胜利是否已经实现。亨廷顿认为不是,他尤其担心西方社会中的「道德败坏」──嗑药、家庭伦理破灭、传统美德沦丧等等──会使其落败。在这点上,亨廷顿与宾拉登等伊斯兰基本教义派倒是意见一致。在世界图像上,福山与亨廷顿一致都把历史的主角视为某些抽象的、不变的、自我圆满的「历史力量」──「自由民主的理念」、「极权主义」、「西方文明」、「伊斯兰文明」等等。而历史则是这些巨灵之间的争斗。
福山与亨廷顿的观点承继着非常传统的十九世纪西方殖民主义的意识型态,而911之后一些右派论者也不再忌讳这点。美国历史学家詹森(Paul Johnson)或许是最露骨的一位。他在《华尔街日报》的评论中倡言,解决恐怖主义的唯一道路就是殖民主义。他回顾了十九世纪历史,宣称唯有西方国家「负起责任」直接统治那些不够格自我统治的国家,才能消灭猖獗的海盗,使自由贸易得以实现。因此,美国应该寻求直接统治产生恐怖份子的国家来为他们「带来文明」。八国联军镇压中国的义和团就是很好的先例(Johnson, 2001)。
亨廷顿∕福山式的右翼观点与其说是某种关于世界局势的分析,不如说是激越的战争宣传。如乔姆斯基等左翼论者一再以各种方法指出:右翼习于忽视西方殖民主义与新殖民主义对受压迫国家人民的掠夺残杀等大量历史事实,以及其对不平衡发展的影响。他们更不会正视西方社会内部愈来愈激化的社会矛盾(Chomsky, 2001)。与单一、刻板化的「西方文化」、资本主义、和启蒙民主价值扣在一起的「现代性」是他们的战斗口号。在现代化的大旗下,反对当前体制的声音都可以与宾拉登一起被丑化为落伍的妖魔小丑。对亨廷顿∕福山式的右翼来说,当前唯一的深刻危机是有人不认输、不愿意接受(「西方」的)现代化的价值。至于「现代化」的资本主义体制本身的矛盾,以及阿根廷之类拥抱「现代化」价值的边陲国家所面对的灾难,要不是不在他们的视野中,就是被视为边缘现象。
他们自己或许能在极为局限的视角中自圆其说。但是,如果我们稍微放大眼界来看,当前的危机不只涵盖宾拉登集团这种反挫势力,出问题的更是被他们称为「现代性」的这个西方主导的体制本身。
 2011年九月十三日,搜救人员于纽约世贸大楼残骸中寻找生还者。(图片来源:Beth A. Keiser/AP)
2011年九月十三日,搜救人员于纽约世贸大楼残骸中寻找生还者。(图片来源:Beth A. Keiser/AP)
第三条路与「现代性」的危机
关于「现代性」的讨论与辩论是1980年代以来西方社会理论界的一个主轴,围绕着启蒙的普世价值、资本主义(及其反题──社会主义)、现代科学与技术等现象的文化、政治、经济、社会体制成为德西达、布希亚、李欧塔等「后现代」理论家的解构式批判焦点。后现代派对于整体性(totality)的批判多半隐含着一种期待,期待一个更多元、缤纷的人类世界。而其他立场的论者──尤其是马克斯主义者与社会民主派──则希望在回应、正视后现代派的批判与愿景的同时,又能够保存启蒙的价值。在下一节中,我会谈到包括沃勒斯坦在内的泛马克斯主义圈子的论述与辩论。在这里,让我们先看看几位当前著名的社会民主派的分析。
冷战结束后的西方社会民主派处于一个尴尬的中间位置。一方面,他们放弃了传统各社会主义流派推翻资本主义、建立新社会的立场,因而必须与当前的资本主义体制妥协;另一方面,战后五十年西方阵营中盛行的以国家管制体制为资本主义带来「人性的面貌」的尝试在资本的跨国力量愈来愈强大之下,似乎愈来愈不可能实现。英国布莱尔首相的「新工党」头号顾问安东尼‧纪登斯(Anthony Giddens)的「第三条路」是这个立场中最著名的口号。纪登斯的德国战友,同时也对德国执政的绿党与社会民主党阵营有着深刻影响的乌里希‧贝克(Ulrich Beck)的评论很适切地反映了这种进退维谷的窘境。
和「历史的终结」的福山类似,911事件带来的战争状态看似对贝克近年来的论述提出了令人困窘的挑战,毕竟,从他1994年的名著《风险社会》以来,他就一直在谈论全球化时代是一个「没有敌人的社会」。现在,至少美国正在努力地到处寻找军事敌人。然而,他看到的是:民族国家之间的对立被911事件消弭了。于911之后发表在英国政论杂志《新政治家》上的文章伊始开头,贝克说:
人们常问:「什么东西可以让全世界团结起来?」有些人的答案是:「火星来的攻击」,在某个意义上,9月11日发生的正是这么回事:来自我们「内部的火星」的攻击。正如预期,至少在几个星期中,争斗中的各个阵营与国家团结起来对付共同的敌人──全球恐怖主义。(2001a: 33)
贝克认为,911事件证实了一条规律:反全球化的尝试只会让全球化更加速。恐怖攻击促使各个民族国家形成了更牢固的「跨国合作网路」。然而,在看似天真地歌颂「反恐怖战争」的言词之后,贝克忧心忡忡地指出,国家(state)以更专断的形式复兴了;在国家安全的大旗下,反民主、反自由的措施被强加在「全球化的输家」(失业工人、妇女、少数民族等等)身上,以便让「全球化的赢家」(跨国公司)独享新自由主义(自由放任)的国家体制。他提出的解决之道,是跨越国族界线,建立一个更民主、更包容的「世界国家」(cosmopolitan state),来保障各种不同民族认同的人群的安全。而「世界国家」的任务不仅是防止恐怖攻击,更在于遏止恐怖行动的源头;换言之,即防止欧美国家之外的人民受到欧美强权的威胁。在这个立场上,贝克与福山、亨廷顿等右派人士是对立的。
「世界主义」(cosmopolitanism)在此指的是在全人类范围中,关注所有人的福祉,同时欣赏、包容各种多元的文化与认同。这是贝克从他的名著《风险社会》以来就一直倡言的,他甚至把他1999年出版的论文集《世界风险社会》(World Risk Society)的序言题为〈世界主义宣言〉。在〈宣言〉中,他把希望寄于怀抱「世界公民」胸襟的各国人民所组成的议题性跨国社会行动2上,尤其是跨国的非政府组织(NGO)。不幸的是,在「反恐怖战争」愈来愈演变成美国小布希政权罔顾国际视听的专断独行的今天,贝克认为911事件带来的「正面」效果显然愈来愈渺茫,而负面影响却是持续不断地发酵。
和贝克相仿,纪登斯的「第三条路」对于国际政治的看法也充满着世界主义的话语。他的口号是「世界性的民主」(cosmopolitan democracy),他的主张是藉着改良当前的联合国、国际法庭、国际货币基金会等国际机构来达成较为民主的、「自下而上」的「全球统理」(global governance),以规范无政府状态的世界市场必将带来的不平等、生态灾难等问题3。同样的,在911之后,纪登斯也高倡重拾包容性的世界主义理想。然而,纪登斯所寄望的理想的实践者却比贝克更现实主义,也更成问题。John Lloyd在《新政治家》上的评论指出,「全球第三条路」的体现正是布莱尔与柯林顿主政下的英美「人道干预主义」外交政策,其实践的例证是1999年美英主导的科索沃战争,其对立面是孤立主义与季辛吉之类的保守派的纯粹利己主义的外交政策(Lloyd, 2001)。从布莱尔政府在近几年的战争中甚至比美国更强硬、更兴致勃勃的鹰派立场来看,这「第三条路」与极右派之间的差异恐怕是夸大其词。对此,《新政治家》的文艺编辑、巴基斯坦作家Tariq Ali(2000)尖刻地指出,从科索沃战争看来,「(布莱尔主政下的)英国事实上没有什么独立性,它的主要功能是提供佣兵来为美国霸权撑腰。」(p. 25)
贝克与纪登斯对于世界危机的观点及其提供的解决之道体现了他们近年来的理论工作,尤其是他们对于「现代性」的批判和对全球化的分析。在贝克与纪登斯的分析中,全球化是一组由微电子通讯科技的突飞猛进、资本的高度金融化与跨国流动化等现象所造成的晚近现象4。在全球化之下,民族国家的地理界线变得愈来愈无意义(在这里,贝克与纪登斯竟然和福山若和符节!)。在世界某个角落发生的事──不管是某国利率的升降,或是某个核电厂的事故──会迅速地影响到其他地方人们的命运5。从而,以民族国家为界线、一国之内的阶级妥协为框架的社会民主体制(或曰福利国家)变得愈来愈不可能。纪登斯称此为「老左派」(主要是战后西方的社会民主派)的消亡,贝克甚至称之为「无工作的社会的到来」,因为前此的福利国家体制是以保障就业及与就业配套的福利措施为中心的。相对的,「非阶级」、「非国族」的全球风险议题──例如环境风险──则成为愈来愈显著的矛盾。在之前的「现代性」的意识型态中,这些风险常被认为能透过菁英主导的科学技术、或是自命为科学的专家系统管理体制(例如国民经济调控)来克服。但是,在深入的分析之下,我们会发现这些风险往往正是这些管理体制追求控制自然、控制社会所造成的不可预见的后果。但是造成深重影响的这些菁英决策者却不见得会分担恶果。他们称此为「现代性」的危机,而呼吁重构更多元参与的、责任与风险和机会相扣的「第二现代性」。他们更认为当前的世界是一个「没有敌人的世界」,唯一的敌人就是现代性体制本身的缺陷。
贝克与纪登斯之间有许多重要的理论分歧,在此难以尽述6。然而,他们的共通之处是值得关注的。他们的论述主体一直是(某种程度上)全称的「全人类」,他们关注的焦点是跨阶级、跨国族的议题,而他们的基本政治关怀在于如何以(修正过后的)启蒙理性价值来处理这些矛盾。他们把危机视为之前较狭隘的科技理性和国族框架下的民主的危机。这个危机是19世纪以来盛行的革命或改革愿景──尤其是社会主义和民族解放运动──所不可能解决的,因为这些愿景都在旧的「现代性」的意识型态中力求建立一个有全观调控能力的体制,即「现代」国家;而这种调控非但不可能实现,更会带来不可解决的灾难。解决之道,在于重构一个动态、多元、包含各种市场和市民社会力量的「统理」(governance)而非统治体制(government)。在他们的分析中,不平等不再来自于剥削、压迫,而是来自于「排斥」;而平等则等于「包含」,包含进这个动态的「统理」之中,当然也包含进据说是竞争而不确定的资本主义市场中。
不管他们如何标志自己,贝克与纪登斯的「风险社会」和纪登斯在此基础上发展的「第三条路」论述事实上非常倚赖古典的自由主义政治理念──多元、参与、互动等等。资本主义市场正是古典自由主义最肯定的体制,也是当前世界危机中最突出的主宰力量。贝克(1999)对于资本主义全球化及其后果仍然抱持担忧质疑的立场。纪登斯,尤其在他回应诸多左翼批评的新作《第三条路及其批评》中,则愈来愈热情地站在布莱尔政府亲资本主义的立场上,因而也愈来愈被批评为假借旧社会民主主义的话语来替反动的新自由主义撑腰。在2002年2月新出版的《工党往何处去?》中,纪登斯甚至站到更右边,抨击布莱尔政府的「反商」政策。(Giddens, 2002)
阿根廷学者佩特拉斯(Petras, 2000)认为,「第三条路」的论述是站不住脚的。它在社会面向上假设阶级斗争已经落伍了,然而事实上近二十年来在先进资本主义国家出现的却是无情的「自上而下」的阶级斗争,是统治阶级千方百计地要取消工人阶级的现存权益;在经济上它假设资讯科技带来的「新经济」已经带来巨大的生产力突破,然而事实上这个突破被大大地夸张了,且90年代的经济增长很大部分是来自金融投机;在政治上它鼓吹市民社会的自由结社,然而却是为了一方面削减国家预算,把先前的国家业务移转给私部门,另一方面瓦解先前的工人阶级政治力量(pp. 33-36)。近年来,尤其是在反全球化运动兴起之后,批判「第三条路」的声音在西方左翼愈来愈多,甚至纪登斯的美国社会民主派同盟Jeffrey Issac(2001)在为「第三条路」的创意辩护的同时,也不得不批评纪登斯几乎完全忽视对不断膨胀的资本的权力的批判。
贝克与纪登斯当然不会不知道这些批判观点,但是在这个危机时刻的反应却是如此天真,甚至(尤其是纪登斯)为当权派辩护。除了立场问题外,他们90年代围绕着「风险社会」概念发展的对现代性的批判恐怕也是一个原因。他们投注了大量的思辩能量在启蒙理性的有效性、可行性的议题上,但是,在作为他们的社会分析的重要基石的当代政治经济分析上,他们却常常不加深思地援引主流派新自由主义经济学夸大的论述──资本全球化的划时代意义、新经济的奇功异效等等。而虽然他们自许为「世界主义者」,他们的视野却是出奇地局限在资本主义先进国家之中。全球不平衡发展之下绝大多数边陲国家的困境鲜少出现在他们的分析之中。
「自由主义之后」与资本主义的终结?
政治经济的分析,尤其是长时距、全球范围之下的世界体系分析,正是沃勒斯坦的毕生事业。在沃勒斯坦看来,纪登斯当作《第三条路》的问题意识的历史剧变──1970年代以来世界资本主义面貌的明显改变、冷战的结束以及社会主义的衰落与新自由主义的兴起──根本不足为奇。
首先,1970年代发生的是世界资本主义体系(而社会主义阵营是这个体系的组成部分)从扩张(他称之为孔德拉提夫循环A阶段)走向收缩(B阶段)的分水岭。被称为「全球化」的经济现象──资本的高度金融化、弹性化、流动化、投机化以及经济的高度不确定性──是历史上每个B阶段必然出现的状况。这个扩张与收缩交替的循环在资本主义的历史中已经进行了许多回合。其次,从70年代开始衰落的、看似与资本主义对抗的社会主义(包括共产主义与资本主义国家的社会民主主义体制)和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其实不过是广义的自由主义意识型态的变奏,而这些都是以「国家发展」为中心的意识型态。而70年代开始这些二十世纪的反体制运动的式微,也同时代表了自由主义的终结。所以,福山之类为西方资本主义霸权高唱着「我们赢了!」的保守派的言论根本是无稽之谈7。
沃勒斯坦认为,事实上,资本主义作为一个历史体系正在走向崩溃。根本的原因正在于它成功地扩张到全球范围,从而激化了三个结构危机:(1)「世界的去乡村化」,即大部分世界人口被卷进雇佣劳动体系、「半雇佣劳动」的劳动力来源枯竭,工资因而上涨;(2)自然资源的枯竭与生态危机使资本无从「外部化」其生产成本;(3)世界的民主化及其所导致的人民对公共服务支出及征税的要求的不断上升,挤压资本的利润。这些因素将使得资本利润的积累愈来愈不可能,进而导致资本主义世界体系最终的崩溃。这些危机不是正常循环中的周期性危机,而是无可转圜的危机8。911事件等纷乱现象,只不过是体系崩解过程中必然会有的「狂乱的震荡」。
「现代性」──现代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意识型态──对沃勒斯坦而言,具有愈来愈互相矛盾的两面性,他称之为「科技的现代性」和「解放的现代性」;前者追求生产力的不断发展,后者则要求普世性的民主与平等。他用这两个现代性的矛盾来解释法国大革命以来曲曲折折的世界政治变迁,并认为二次大战后「自由主义」的各个变体──资本主义中心的「福利国家」、苏联集团的社会主义制度、第三世界民族解放运动的国家发展方案等──都是试图调和这个矛盾的尝试。在较早的著作中,沃勒斯坦及其他批判的发展理论学者把这些藉由大致在资本主义定义之下的国家发展与全民福祉联系起来的方案称为「发展主义」;而在近十年来,沃勒斯坦特别依赖「繁荣」与「民主」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来论述发展主义以及当代资本主义的殒落。
尽管沃勒斯坦与福山、大前研一、贝克、纪登斯等论者立场迥异,他倒是同意他们的一个观点:以民族国家为范围的改革措施不再可能。这倒不是由于当前时刻的什么特殊性,而是由于在本质上就是世界性的现代资本主义体系中,国家这个政治结构本来就不可能自外于世界经济,因而不可能是革命的有效工具9。法国大革命以来,保守主义、自由主义与社会主义尽管有种种立场的对立,却一致以国家为最重要的施为渠道,这是他所称的「自由主义的意识型态」。他认为1968年是一个重要的转捩点,因为老左派「先夺取国家政权、再透过国家发展带来变革」的策略在世界的各个角落被人民唾弃;而当前以「反全球化」为名的世界性反抗运动是有希望的,正是因为它与之前的刻板的革命运动不同,是世界性的、真实地跨越了南北界线,它的组织松散而包含各种多元的倾向,而且是战斗性的,他称此为「榆港精神」(Spirit of Porto Alegre)(Wallerstein, 2002a: 18)。对于「第三条路」之类的中间偏左派,沃勒斯坦呼吁反抗者要努力逼他们实现自己的平等、民主、共同富裕等道德承诺,因为这些承诺是资本主义不能负担的;每实现一分,资本主义的终结就近了一步。
沃勒斯坦略带耸动的立场与分析当然会受到各方的挑战,尤其是来自左翼的质疑。美国左翼期刊《每月评论》的编辑部就指出,沃勒斯坦论述的资本主义无可转圜的结构性危机是值得怀疑的。成本上升导致的利润危机往往会被生产力的增长所补偿;「世界的去乡村化」并没有导致「世界的民主化」之下大批向资本争夺利润份额的劳动者,反而是出现大量的失业、贫困、和两极化;而「税务国家的危机」(Schumpeter (1991)语)恐怕是由于阶级社会中的经济制度要求国家不能太损害资本利润,而不是由于工人阶级要求的愈来愈多10。《每月评论》编辑部认为,在不清不楚的分析下,沃勒斯坦有可能犯了「左派精神乐观主义」的错误。他一再提到左翼运动面临了世界体系的大转向。但是,转向什么?他却没讲明(Monthly Review, 2002)。
对于《每月评论》编辑部「转向什么?」的质疑,沃勒斯坦以一贯的乐观主义回答:端视我们的作为(Wallerstein, 2000b)。这也是他在台北的演讲中强调的,在体制崩解的时刻,人类的集体能动性会产生极大的作用。坦白说,我也认为这是一个不清不楚的回答。精神上或许令人振奋,但知识上有所欠缺,更难以指向一个实践的纲领。到底在这个危机时刻之下,在「榆港精神」之下复兴起来的全球反体制运动要争取把人类世界推向何方?
许多其他的左翼论者倒没有如沃勒斯坦一般谨慎地拒绝指出方向。例如匈牙利裔英国学者梅札洛许(Meszaros,2001)就毫不保留地引用二十世纪初罗莎‧卢森堡的著名文章的标题作为他的近作的书名来描绘二十一世纪人类必须抉择的两条路:「社会主义,还是野蛮状态?」11。同样地,与三十年来与沃勒斯坦一同致力于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研究、时任塞内加尔「第三世界论坛」主任的埃及学者萨米尔‧阿敏(Samir Amin)也把这个口号放在他对二十世纪的政治经济学的总结文章的结尾。(Amin, 2001)
认同十九世纪以来社会主义运动的遗产、努力透过批判地继承这些遗产来重构当代的反体制运动,这是许多当代左翼学者的志业。沃勒斯坦或许在感情上会同情,在实践上却不同意这个取向。一方面,他在政治立场上明显地比其他社会主义者更拒斥法国大革命、十月革命、民族解放运动等之前的反体制运动的遗产。另一方面,大部分社会主义学者们的分析尺度(尤其是时间尺度)明显地与沃勒斯坦所使用的不同,从而其分析的焦点也不同。沃勒斯坦习于用15世纪以来6、70年为期的扩张与收缩交替的长波动(孔德拉提夫循环)以及五百年不断的曲折但单向发展的趋势(「解放的现代性」对「科技现代性」的挑战)来分析,因而他所描绘出的当代局势,非常矛盾地,同时是无须大惊小怪的、发生过许多次的周期现象的一部份,又是五百年来发展气数已尽的末世景象,因而反体制运动的实践同时可能是徒劳无功(因为不过是历史循环周期的一部份),又是充满各种前所未有的可能性(因为现在是体制终结的时刻)。
而其他的马克斯主义者对当前的「全球化」的分析常以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与帝国主义兴起的年代做为参考座标,以1945至1973、74年的扩张期(和美国霸权期)和其73、74年迄今的收缩期(和美国霸权动摇期)作为分析的焦点。他们的分析常常着重于指出二十世纪末与十九世纪末的帝国主义高潮期的异同之处,因此倾向于批判地继承十九世纪以来反帝国主义、反资本主义的运动遗产。生态马克斯主义者佛斯特(Foster,2002)对当前全球化的分析是一个很好的例子。佛斯特主张继承并发扬列宁以来对帝国主义的分析,用十九世纪末垄断资本的兴起及其藉由市场扩张来解决生产过剩所带来的积累危机的冲动来解释二十世纪末被称为「全球化」的这一波全球政治经济变迁:资本积累速率的降低、新一波的垄断化、以及资本积累过程的高度金融化。他试图阐明当前的全球化危机背后的「看得见的手」──国际垄断资本及帝国主义国家及其在受压迫国家的政治附庸──来为反体制运动树立清楚的对立面。
沃勒斯坦在宾汉顿大学社会系的同僚佩特拉斯(Petras, 2002)在榆港世界社会论坛上发表的对911之后的世界局势的分析一方面援用了沃勒斯坦式的世界体系分析的洞见,同时又提供了反体制运动需要的比较清楚的时势分析。与沃勒斯坦类似,佩特拉斯认为「全球化」是资本主义的扩张与收缩周期的一部份,而1970年代以来的全球新自由主义风潮是核心国家的资本为了应付收缩期的困难而发起的新一波扩张行动(Petras & Veltmeyer, 2001: Ch. 2)。然而,新自由主义并未带来资本主义的世界大同;相反地,解除了扩张限制的垄断资本很快地造成了其体系内部矛盾的激化。第三世界的新自由主义体制纷纷破产、核心国家的生产过剩、利润率下降危机又无法获得任何缓解、世界性的长期经济停滞使得荣景的假象只能依靠着核心市场的金融票券投机来撑起、而资金往核心国投机市场的流动又进一步加剧了第三世界的经济危机,在如阿根廷等各个角落导致了政治危机。2001年10月7日美国发动全球范围的「反恐怖战争」标志着帝国主义从新自由主义走向「新重商主义」的转折。
佩特拉斯指出,当前帝国主义的「新重商主义」有如下几个特征:第一,藉着昂贵的战争展现军事实力,撑起投机资本对核心国家金融市场的信心(1007之后,纽约股市一路上扬);第二,压迫第三世界国家开放市场,同时提高核心国家的关税与对本国产品的补贴,来把危机转移到第三世界(当前已开发国家对第三世界产品的关税是对其他已开发国家产品的关税的四倍,核心国家对出口农产品的补贴在2000年高达2,450亿美元);第三,第三世界国家的政权愈来愈强势地主导经济活动,使其向出口活动倾斜,而这些出口最终是有利于帝国主义经济的。佩特拉斯认为,911事件之后摆在世界反体制运动面前的,不只是来自帝国主义军事力量更严酷的暴力威胁,更是新自由主义代理政权普遍地失去正当性,而帝国主义对世界人民的威胁因此会更如实地展现出来。在这个基础上,他呼吁把「反全球化」的运动提高到「反帝国主义」。只有反帝国主义的人民运动的政治力量能够决定世界体系的未来12(Petras & Veltmeyer, 2001: Ch. 2)。
佩特拉斯的分析所指向的政治实践很明显地是站在十九世纪以来的社会主义与民族解放运动的基础上,而这却是沃勒斯坦认为已经死亡的道路。到底这条道路是否能够有效地服务于二十一世纪的世界人民反体制运动,最终当然必须由历史来决定。但是,至少我们可以看到,佩特拉斯的论述这种扣紧现实运动实践的特性,是沃勒斯坦的长时距分析所无法提供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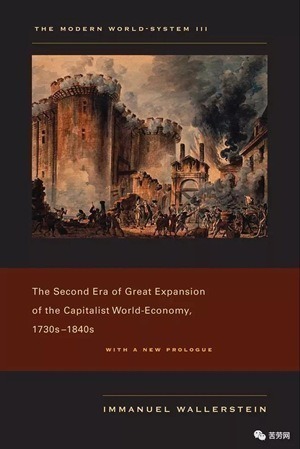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册书封。
《现代世界体系》第三册书封。
时势与理论
沃勒斯坦对于当前危机的分析与其他当代左翼论者相较,显得大而化之。他集中精力在提醒人们不要把视角局限在看似独特的一时一地的状况,而要尽力从整个资本主义世界体系的长历史来理解当前的各种课题,但是他本人却并未提供比较完善的时势分析,而只提供了一些旨在引起争议的命题。这个局限恐怕不是由于力有未逮,而是一种论述姿态与取径的抉择。
在1999年发表的〈世界体系分析的兴起及其即将到来的衰落〉中,沃勒斯坦回顾了以他为核心人物的这个学派的成就,以及世界体系分析在取得各方重视时其词汇如何被误会挪用。他并且断言,世界体系分析的有用性正在消失,其原因有三:第一,世界体系分析不是一个理论,而是一种观点,尤其是一种对于以往局限于民族国家的分析单位、局限于十九世纪中以来西方社会科学的学科分际的主流现代化理论的批判13。批判主要是破坏性的,而不是建设性的。第二,批判论述很容易被收编,因而失去原有的锐气。第三,在三十年来的批判中,世界体系分析作为一个社会科学的运动,从批判当代世界经济中边陲地区的状态、到批判现代世界的史学、到批判史学背后的理论、到批判理论背后的知识体系,一重又一重似乎永无止境地抽丝剥茧之下,他发现问题似乎更深刻地深植于资本主义世界经济的思想体系之中(Wallerstein, 1999: 197-199)。因此,沃勒斯坦认为,世界体系分析的工作者应该致力于比以前更深刻的对当代社会理论的批判与重构。
作为一种批判,我们可以看到沃勒斯坦本人的论述以及他扮演了重要角色的批判的发展理论很有效地攻击了局限在西方中心视角中、围绕着「现代化」意识型态、缺乏深而广的现实政治经济分析的各种论述。沃勒斯坦的观点有助于我们看到福山、亨廷顿等右派的谬误,以及贝克、纪登斯等中间派的局限。然而,作为指导实践的理论,沃勒斯坦的世界体系分析是不足的。或许,我们应该,如他本人所建议地,如实地看待沃勒斯坦到目前为止对当代社会思想的贡献,即:「破」远大于「立」。世界体系分析汗牛充栋、贯通古今的大量著作很容易引起读者的敬畏之情。然而,要有效地运用这些理论与历史工作所获致的洞见来实现沃勒斯坦与无数世界人民所共享的愿景──一个更民主、更平等的世界,则有待更多人用热情而批判的态度来看待沃勒斯坦的贡献。
注释:
1.赵刚(2002)提供了一个对当代全球化辩论的丰富、多面向、又清晰的介绍,并略论了这些辩论对于台湾左翼实践的意义。
2.贝克称这种行动为「次政治」(sub-politics)以与前此以民族国家政权为框架的政治作分别。
3.关于纪登斯这方面的主张的简要版本请参照《第三条路》(郑武国译,台北:联经,1999)第五章。关于科索沃战争等西方「人道干预」政策的批判车载斗量,例如: Chomsky (2000).
4.在这点上,他们大量地引用关于「后福特主义」的弹性积累体制的论述。参见:Amin (ed.) (1994) 之中的论点。
5.当然,纪登斯与贝克对新自由主义夸大的「全球一体化」的提法是有保留的,见Giddens (1999), pp. 32-35; Beck (1999a)。
6.关于贝克对纪登斯的批评,可参见Beck (1999), Ch. 6。
7.对于那些歌颂西方资本主义成就的声音,沃勒斯坦在其《现代世界体系》的中文版序言中扼要地说:「创立资本主义不是一种荣耀,而是一种文化上的耻辱。」(Wallerstein, 1998: 1)
8.沃勒斯坦在近年著作中多次重述这些观点,参见例如:Wallerstein (2001),及本书其他章节。
9.这个以「全球」为唯一重要的分析尺度的立场,David Harvey称之为「全球主义」(globalism)并批评其忽视了不同空间尺度中的实践的重要性。对于「全球主义」的悖论,请见赵刚(2002)。
10.关于征税是否压缩利润的问题,值得一提的是,Issac (2001)观察到,「第三条路」及新自由主义的改革一致地要取消累进税制。Giddens (2002)不悦地指出,英国最富有的1%人口缴纳了20%的所得税。他因而要求减税。但是,反过来看,这也恰好反映出所得两极化的严重程度。
11.「社会主义或野蛮」也曾经是现今后现代主义派的健将Castoriadis和Lyotard主持的期刊的名称。但是两者后来都放弃了这个立场。见Kanelis (2000)。
12.对此,佩特拉斯举出近年来愈来愈激烈的哥伦比亚内战,以及巴西、阿根廷的农民与工人运动作为例证。
13.关于华氏对学科分际的批判,参见Wallerstein et al. (1996)。
长按二维码支持激流网

为了避免失联请加+激流网小编微信号jiliu1921
 (作者:陈信行。来源:苦劳网。责任编辑:黄芩)
(作者:陈信行。来源:苦劳网。责任编辑:黄芩)





